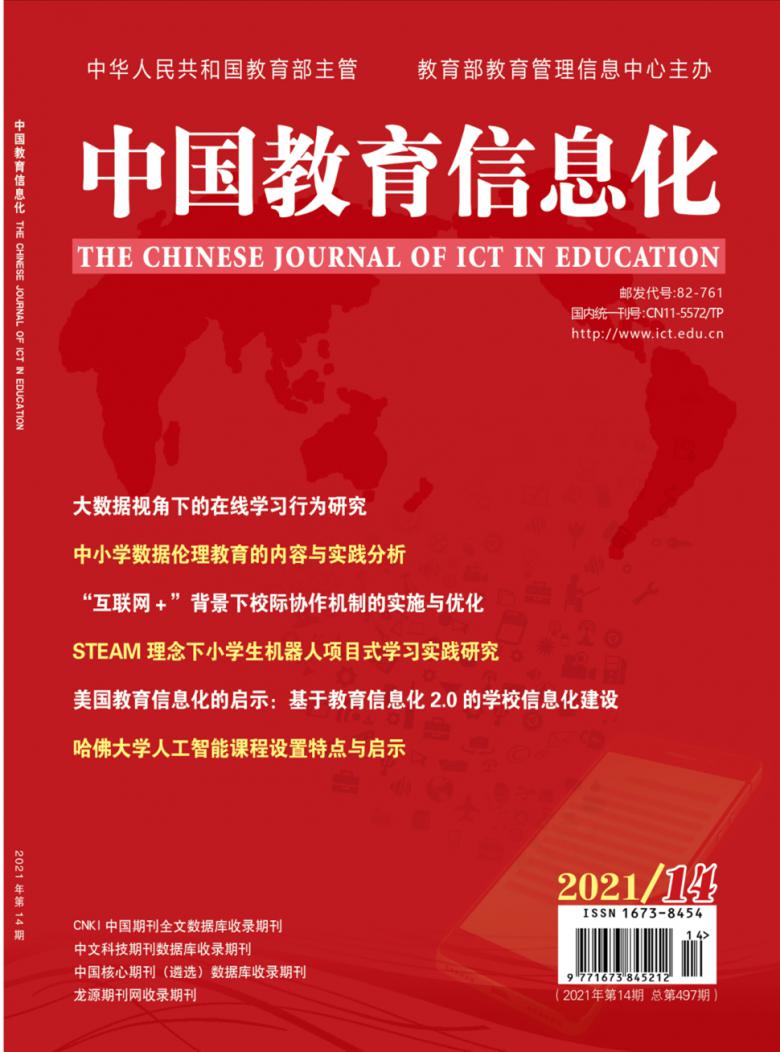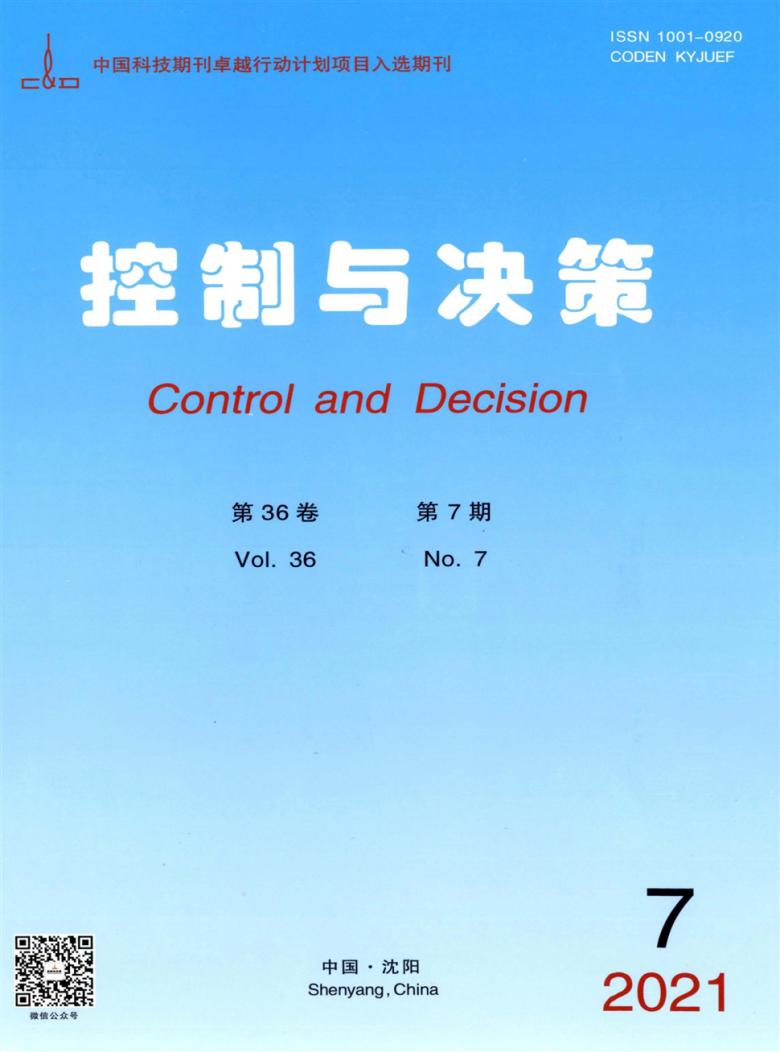摘要:教育学界一直关注教育学研究方法论建设,却成就甚小。构建研究方法论的前提是各种研究方法在特定学科内形成了某种逻辑联系,而这种逻辑联系恰恰是教育学所缺乏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功能是确证判断。确证判断的学术合法性前提是研究本身的可重复性,而研究本身的可重复性是以研究对象的可重现性为前提的。有了可重现的研究对象,学界才可能针对它展开各种判断以及基于事实的主体间理性交流,由此生成学科知识体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空虚最根本的根源在于教育学没有找到正确的研究对象。教育现象、教育活动、教育问题都不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抽象的教育系统才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系统的知识体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自然是发现该知识体系的方法体系。在尝试创生这个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提出过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和IIS图分析法。能提出这些独创的研究方法得益于将教育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当然,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最终成熟需要更多、更持久的教育系统研究经验的积累。
关键词:研究过程模型,研究方法,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IIS图分析法
研究的过程模型
据说“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的方法”,按照这个逻辑,教育学的本质是否就是教育学研究方法呢?无论如何,教育学界一直关注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几乎成了教育学研究的专门领域。然而,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成就却难以让人满意。
从功能上讲,研究方法只解决信息的发现、创生、收集和处理问题,却不能解决信息的防伪与误用问题。信息防伪是指消除信息隐蔽,使得数据造假(比如叙事研究中的编故事和实验研究中的伪造数据)变得即使无法立即识别也不会对理论的进步造成误导;信息误用是指不顾及研究方法的适用条件,强行采用某种研究方法武断地得出可疑的结论。所以,研究方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某种操作流程,我们需要在更大的框架下理解它。
人类通过研究意欲何为?无非是:主体间地还原事实、揭示意义和把握真理。形而上一点说,就是理解这个世界。事实并非就放在那里等待直观,事实源于事情,是人们对事情做了某种取舍所产生的东西,是无限杂多中的特定取样。事实不是现成的事物,而是特定观察(含操弄)的结果,其目的就是将它与真理和意义建立某种对应关系。事实对真理提供支持性证据,同时也参与意义的生成与组织,意义是对存在的解释,离开了事实,就近似胡说八道。在终极意义上说,意义和真理与事实之间都构成了解释性的支持关系,只不过事实居于基础位置,人类理解世界的现实基础是对事实的绝对服从,真理与意义都不能罔顾事实,必须与事实相一致。同时意义系统、真理系统也需要内在一致。与真理不同,意义是对人类精神客观化物的解释。那个客观化物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生成的,所产生的解释又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种解释不具有唯一性,而只能属于效果历史。意义是先在的人类精神通过客观化物与后来的人类精神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相对性、又是意义随历史展开的一部分,因为它与历史文化以及相应的个体有关,与时代以及个人的关切有关。意义是随着历史而展开的,所以对于意义我们不能强求唯一性而只能追求丰富性。对待真理系统,我们说去伪存真,这是人类实践所需;对待意义系统,我们通常不这样说,而是希望获得更多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层次的丰富性,这是人类精神生活所需。但任何解释也只有满足内在一致、不罔顾事实、也不与已知真理相矛盾,才能为意义的丰富性做出贡献。这种内在一致性、与真理和事实不相矛盾,可以看作是一种弱意义上的真。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说某个解释是真理,而说它有道理。
事实、意义和真理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关于世界的真相由真理、事实和意义构成。真相不可能是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真相是属人的真相,是一种世界与人的关联。真理的唯一性与意义的丰富性都是人类所需,二者并不矛盾。真理和意义无法脱离事实而存在,同样事实也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处于“事实—真理—意义”的系统之中。与真理与意义都无所呼应的就不叫事实。但一旦与真理或意义相呼应,与真理和意义一样,事实必然是主体间的东西。
研究与真伪和意义相关,因而一定是有用的,最起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有些结论还直接支持我们的行动而具有世俗功利之用。从这个角度看,实用主义的浅薄之处就在于,它过度强调可预见的和针对特定人群的用途,而忽略了真伪和意义才是实用之基础。在研究阶段看似有用实则无用或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我们讨论研究时,勿需着眼于是否有用,只需着眼于真理和意义的发现。
新判断的生成是研究者个人智慧的表现,其时间成本不可预期,又属于智力上的创新,故而不可能用方法约束,只能是个人造诣所致,且具有猜的性质。只有在确证阶段,由于判断已经清晰,故而需要用研究方法约束确证过程,提高其确定性。由于研究方法具有明确且固化的操作过程,因此我们不但可以降低确证过程的社会成本,也可以使得这个过程公开透明,方便他者重复这个过程。他者无法重复新判断的生成过程,因为它是私人的;但他者需要重复判断的确证过程,使得这种确证成为公共的。成功的公共确证过程使得新判断由私人主观提升为社会性客观,达到主体间理性的水平。不同主体采用同一研究方法的特定过程都能成功确证的情况下,新判断才能被真理或意义系统所接纳。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及去伪存真或意义丰富性的问题。不经过特定方法就将个人主观见解或个人经验性观察上升为事实、真理或意义,是不具备学术合法性的。可重复的确证过程是研究结论达到主体间理性的必由之路。意义的确证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意义的显现过程同时也是说理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文字的方式变得可以重复(重复阅读),这也是能做到的最强的意义确证方式。而真理的确证,特别是经验真理的确证,需要重新构建作为证据的事实,这就要求研究情境可重现、事实数据可重复获取,这是因为事实是前景、情境是背景,二者联系密切。事实是特定观察操弄的结果,事实能够在何种精细完整的水平上被获得,受制于当时人类实践的总体水平。事实是有尺度的,自然整个研究的可重复性也是有尺度的,它不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可重复。
只要一种操作过程直接针对特定命题和意义的确证,它就是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其运用的合理性无法由它自身提供,孤立地讨论研究方法的形式特征是不得要领的,而且在一个具体领域或学科中讨论与领域或学科情境无关的研究方法是粗浅的。研究方法是工具,目的则是确证那些判断。所以,不是新方法而是新判断才让人兴奋。新判断可以被重复确证才是研究的关键。可重复是一项研究最基本的要求,至于是定量还是定性、研究者是否进入现场、是否参与其中、是采用人工观察还是仪器设备测量、是受控实验(或试验)还是自然情境的观察调查以及数据的处理方法,等等都是技术性问题。但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绝不是自然而然的。无论是意义还是真理的发现,确证过程可重复的前提只能是:意义和真理所针对的那个对象是一个主体间可重现的对象,而非奇迹条件下的偶遇。真理和意义都是关于某个研究对象的,只有研究对象可重现,人类才能发展出关于它的真理系统和意义系统。
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成就
从目前来看,教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哲学思辨范式”“科学实证范式”和“诠释规范范式”的转换历程。可是有趣的是,每次研究方法的更迭与研究范式的转换都伴随着改变教育学命运的承诺和失败。这种更迭与转换一方面对旧方法旧范式进行大肆批判,抱怨它们一事无成,同时强调新方法新范式的优势,另一方面新方法新范式除了最初的让人眼前一亮之外,与旧方法旧范式一样,等待更新的更迭与转换。最终我们只得到了各种研究方法范式在教育学研究中的“尝试”而不是数量逐渐增加的成功范例,这些尝试只是按照方法或范式的样子、遵照方法的形式特征,做了一些“研究”而已。如今人们发现没有哪种方法范式能独领风骚,自然会强调“综合运用”的立场。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几乎成了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辩证绝杀。当然这也说明,在这个方面我们无话可说,只有辩证法的空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学界对研究方法的讨论是浅化的,几乎从不涉及何以达到主体间理性的问题。所以,教育学看似声称可以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实则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论——那些研究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的组织运用逻辑。
既然我们对于教育研究的内在逻辑认识不清楚,在研究方法使用上随意而为,其结果自然在理论上无所收获。事实是,无论哪种方法或范式都没能挽救教育学,“教育学研究成果精品少、无积累,研究基础没有增厚,缺乏实质性进展”,一如既往地缺乏实质的知识和意义系统的积累。就是说,那些研究方法并没有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内用来确证过什么知识判断,因此并没有升格为教育学研究方法。思辨当然是教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但思辨范式对教育学的贡献却泛善可陈。这主要是因为,思辨是在范畴、概念基础上进行的,是概念和范畴的自否定运动,可是由于教育学缺乏自己的核心概念体系,思辨降格为思考。对于教育学来说,仅仅靠思辨就能独立处理的问题也不会是很要紧的理论问题。教育学的实证范式是失败的,这是因为教育学的实证研究陷入了有效性陷阱。最典型的是通过准实验及其对比来检验方法模式的有效性。可是方法模式原本不是知识,它只是行动规范,与知识的真伪无关,却要通过“实验”检验。对于教学而言,方法模式是否有效,其证据当然是学生绩效的分数及其变化或分布是否令当事人满意。这种令当事人满意的证据完全不具有客观性,当事人不同,判断会完全不同。除了证据无效之外,从效果出发而判断教学方法模式的有效性在归因上异常困难,对比班和实验班之间严格来说根本不具有可比性,更何况若想证明某种东西的有效性,一次准实验只相当于一个(或一对儿)样本,不足以证明啥。更为关键的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确保样本是符合那个方法模式的,是有效样本。教育学的解释学范式是失败的,这是因为教育学所关注的教育活动之中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人类精神客观化物。解释学所面对的解释对象是人类精神客观化物,它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历史沉淀物。当下发生的教育活动中有什么东西能进入历史?进入历史需要时间,它的意义更是需要时间距离才能看清,发生的当下就要解释有何教育学价值?如果不能进入历史,解释学范式就毫无用处。解释学范式看似简单,实则更加难用,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本正经地胡说,追求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糊涂境界。
总之,无论是真理还是意义,教育学的生产能力皆无,我们便缺乏这些研究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真实体验,我们对教育研究方法的教育学特异性便无话可说。究其根源,其实不是研究者个人的事儿,而是因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定位错误。是由于研究对象不具有可重现性,才使得相关的研究无法重复,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无法达到主体间理性,自然无法使得个人主观判断上升为理论(真理与意义)。没有了理论,其研究方法自然没有机会形成具有教育学特异性的体系,教育研究方法论自然是虚无的。教育学研究方法运用的内在逻辑其实就是教育学理论逻辑,没有了潜在的理论知识所隐含的内在逻辑,教育学研究就会显得“束手无策”。求诸于“研究者的态度与能力”,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式”,以及喜新厌旧地或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并不能挽救教育学。教育研究具有描述、规范、解释和批判四种基本功能,这是很大的误解。具有描述、规范、解释和批判功能的不是教育研究而是教育学理论!教育学理论知识的生产首先不在研究方法,而在于研究对象。一旦有了正确的研究对象,人们即使借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也能对它进行探究,积累相关知识,当知识足够丰富,就有可能创造出独特的研究方法,即使没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妨碍建立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