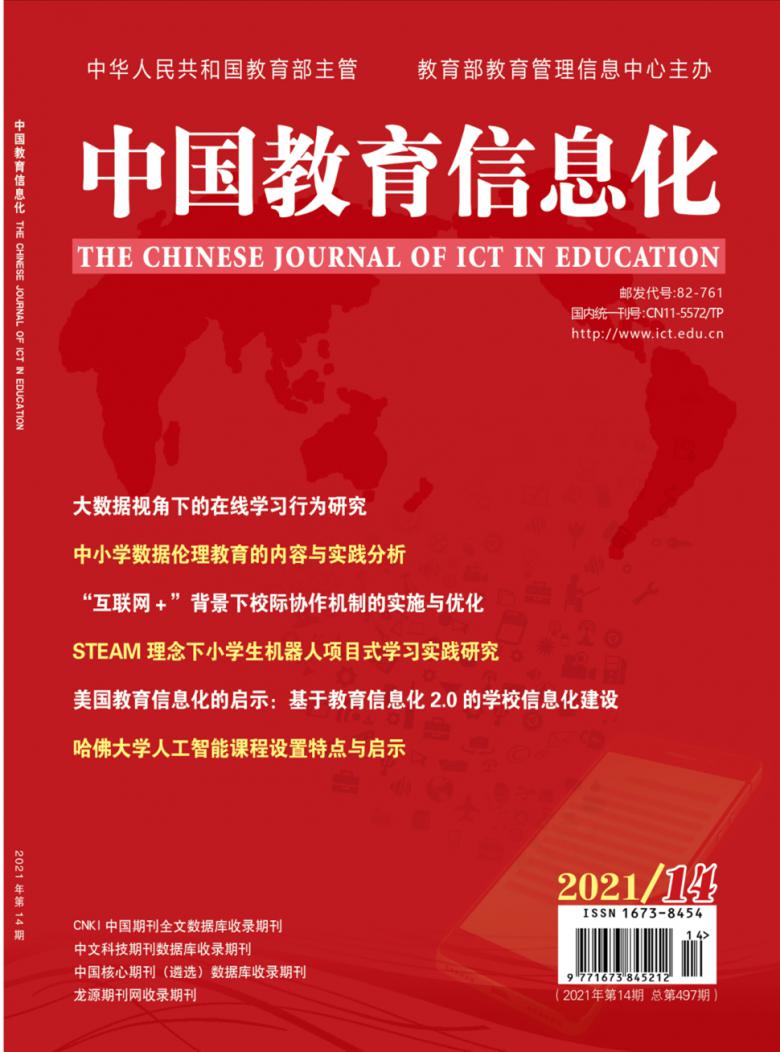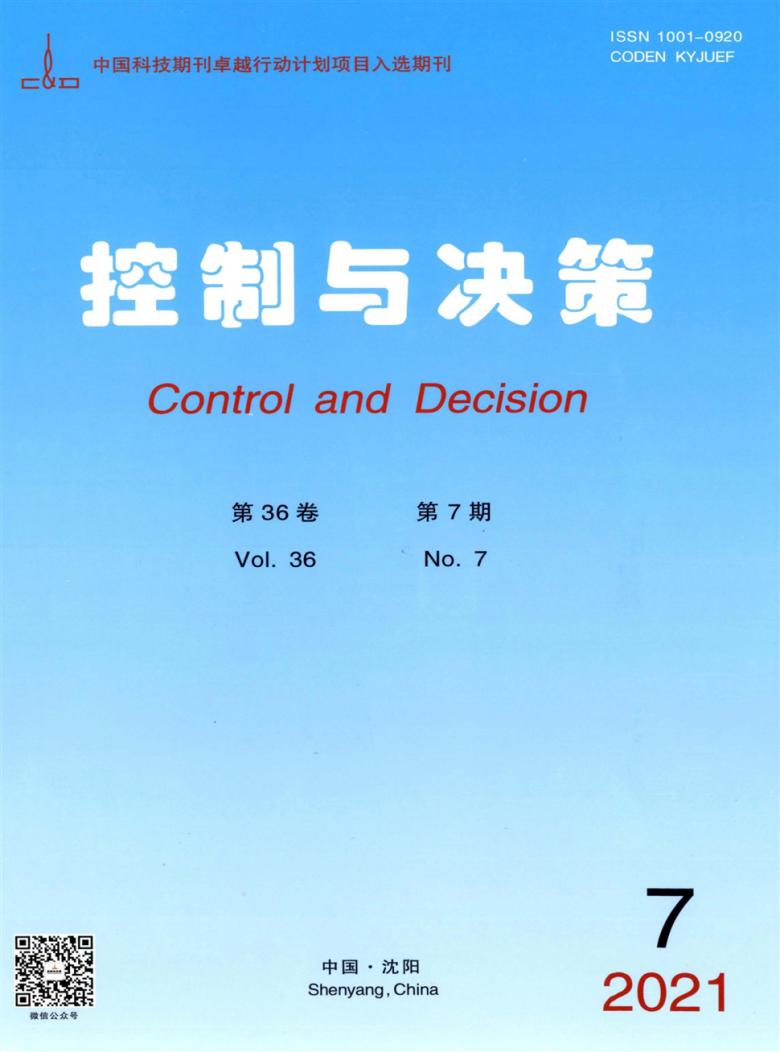摘要:从人类文明史上看,法典在凝聚社会、维系秩序、塑造文明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复杂的智识活动,法典编制既凝结着人类的经验与智慧,也映射着时代与社会的现实需求。在美国,从《纽约州民法典》的起草到《统一商法典》的颁行,“民法典”的编制经历了百年跌宕沉浮的历史进程。有诸多法学家和法律人,如菲尔德、卡特、霍姆斯、卢埃林等,参与其间,无论支持、坚守,还是反对、转向,均围绕着法典编制展开了深入的思想对话与法理辨析,不仅为普通法背景下美国式“法典化”道路提供了极具本土色彩与开创性的思考,而且也为当今世界各国法典编制与法治发展树立了一个可资对比与反思的智识参照。
关键词:美国“民法典”,菲尔德一卡特的论辩,霍姆斯的转向,卢埃林的贡献
一、引言
法典(Codex),从语源上讲,约始于公元5至6世纪的古罗马法,如《狄奥多西法典》或《优士丁尼法典》;从概念上讲,即法律的汇集、全编或者修订,是一个经由立法权威科学编排、正式颁布的完整的实证法体系。纵观人类历史,在社会的凝聚、秩序的维系、文明的塑造等方面,法典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从历史的横断面来看,法典的编制及其作用的发挥往往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法典的规范体系、规则的逻辑关系、法条的语词表达、当时的法律状况、既有的习俗惯例、民族的道德情感、利益的权衡取舍、价值的冲突妥协、社会的现实需求等,这些因素制约影响着法典的编纂、颁布与实施。但若换到历史的纵切面来看,将“法典”放在人类社会一个较长的、甚至跨越结构变迁的时期里进行观察,则会发现,秀论是在不同时期或类型的社会秩序中,还是在社会秩序转型或变迁的过程里,对“法典”及其作用的现实需求不同,自然也会出现形态各异的“法典”;一同时,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对社会秩序的不同认识,也会使人们对“法典”及其作用形成不同的态度和观念。
任何一个法律概念或命题的证成,都无法脱离特定的语境或社会环境,“法典编制”也不例外。相对于欧陆成文法国家而言,在一个兼具普通法历史传统与联邦制政治现实的国家中,“法典编制”面对的更多的是困难和阻碍,而不是顺理成章或者水到渠成。然而,自19世纪中期伊始,美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1857至1952年,围绕着“民法典”编制,许多法学家与法律人参与其间,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争辩与实践,直到《统一商法典》正式颁行。从整体上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①法典化的初步尝试,以菲尔德为代表的立法派付出了许多努力;②法典化的挫败,以卡特为代表的反对派与以霍姆斯为代表的实用派抑制了法典化的努力;③法典化的复兴,以卢埃林为代表的改革派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法典化运动。在这幅由多元法律思想镂刻的时光画卷上,既有菲尔德以“法律科学”为奠基的宏大雄心,也有卡特凭借“历史研究”而展开的理性批判;既有霍姆斯从“优雅法典”的梦想者迈向实用主义的决然转身,也有卢埃林熔铸德国法精神与现实主义于一炉的执着贡献。其间,各种理论和思想在论坛上相互冲撞、交锋,在实践中彼此对话、融合,时至今日,以《统一商法典》(1952)为代表的法典编制,在美国法律思想与实践中,已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位置。
本文正是将研究的视野放在近一个世纪围绕美国“民法典”编制而展开的学术探讨与思想争辩上,旨在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法律制度、社会需求与法律思想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初步的考察与检讨。具体而言,首要问题是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是否需要编制法典,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应当编制什么样的法典,以及如何编制这样的法典;在探讨上述问题的过程中,还会涉及一些基本的法理学问题,例如,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比较,法典在特定时期发挥的作用,法律究竟是什么,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探讨驳辩,不仅丰富着人类的思想、影响着法律的实践,而且也给当代人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性参考。法典的编制、法律的生成与进化是凝结着人类普遍经验与智识的产物,故而,秉持“它山之石,可以为错”的态度,从比较法或法律史的视角,认真观察、理解异域法律的制度、实践与思想,或许有助于对我国当前法典编制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二、普通法的“法典化":菲尔德与《纽约民法典》
相对于美国此前的历史来说,自19世纪50年代起,随着工业增长的加速,进一步改变了美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例如,1820年以前,美国的大多数商法问题都来自海上贸易,因而,统一的联邦法律规则对个案贸易的每一次适用,都相当于确立了一项全新的一般商事法律规则。为了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商法在1825至1850年间得到了迅速扩展,以至于仅仅依靠联邦法院的海事管辖权,已经无法有效规制整个商业活动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节点上,出现了斯威夫特诉泰森案(Swirl秽.Tyson),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试图通过判例确立联邦法院对商业纠纷或诉讼的专有管辖权,维持法律的一致性和确定性,避免因多元管辖而有可能造成的对商业发展的潜在阻碍。虽然斯威夫特案的判决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对法律发展基本一致的需求,但从随后的一些司法判决来看,仍未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经济与“商业实践带动着法律的演进”,这一时期,大多数干预经济与商业活动的政策和规制,是由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作为经济、商业与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纽约州自然引领了当时的经济与法律实践。就在威斯夫特案判决15年后,纽约州法典起草委员会成立,从而标志着一种全新法律调整思路的开启与尝试。
为了摆脱当时混乱不堪的法律状况,建构一个和谐统一的法律体系,根据州议会1857年4月6日法案,成立了纽约州法典起草委员会。成立伊始,法典起草委员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19世纪早期复杂的法律现状,阐明编制法典的重要意义。对此,菲尔德(DavidD.Field,1805~1894)以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律状况为参照,指出编制法典是时代与现实的需要:
此时我们法律的状况,既不同于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也不同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法。从《十二表法》时期到查士丁尼时代,罗马人的政策和法令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增加了许多新的、各种各样的法律,随着商业活动的拓展、共和国和帝国的扩张、社会关系的改进,以及不同地域和国族的法律冲突,大量判决变得异常复杂,因而迫切需要一部精简的、重构的法典。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同样的情况。
不同的市井自有不同的人情世故,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也不例外。法律混乱无序,夹杂着许多互不相称的因素:撒克逊人与诺曼人的习俗、封建法与罗马法、地方惯例以及相互之间存在分歧的各种法庭裁决;此外,还有衡平法、海事法、教会法;即便是共同适用的法律,既有来自制定法的,也有来自习惯法的。然而,社会正在经历变迁,在菲尔德看来,当时的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式各样的“法律和法律意见数量众多,卷帙浩繁,[律师]既无力购买,也无力领悟”,传承自英格兰的普通法“仍散发着封建主义的气息”,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这个理性的时代”。许多美国律师对日益庞杂的判例法表示不满,迫切希望能简化当时的法律并予以系统化。例如,斯托里(JosephStory,1779—1845)就认为判例法的迅猛成长是一场“令人恐惧的灾难,正在威胁着我们,不是把我们葬于坟墓中,而是把我们埋在法律的迷宫里”。基于对19世纪早期美国法律状况的判断,菲尔德指出:
法律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某一个原创的法学体系,如果仅仅基于理论而创建,没能考察国族的性格、习惯、传统、惯例,那将是失败的。关于国家治理和法律的科学是不断进步的;新的法令源自需求,或者经验的暗示,而将正义规则适用于人类事务,则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正是怀着这样的使命感与雄心,菲尔德走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法典化”道路。为了使法典编纂能始终保持一致的路向,菲尔德认为,在创造或者修正一个国家的法学理论时,应当以促进以下两个目的为宗旨:一方面,简化既有法律形式,使之简明易懂,化解疑问,解决争论不休的问题,消除无用的差别;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判断或者他人的经验,可以清晰地表明这样的法律修正。
在明确基本的思路与方向后,法典起草委员会就需要拟定一个具有可行性和开放性的框架结构,作为法典编纂的具体指南。为此,菲尔德拟定了法典体系的编制方案:首先,将全部法律划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其次,实体法又包括政府与政治关系、财产与个人的关系和权利、犯罪与刑罚——分别对应于政治法、民法和刑法;最后,程序法包括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在致加州律协的一封信中,菲尔德指出,正在为纽约州起草编制的法典体系主要由《民法典》、《刑法典》、《政治法典》、《民事程序法典》、《刑事程序法典》构成。
“民法典”的编制,原本旨在让美国人拥有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法典,实际上,也恰恰是一次使普通法法典化的伟大的智识尝试。1865年,菲尔德提交了最后一版“民法典”草案文本(共2034条),涵盖个人权利、法律关系、财产和债,以及与上述内容相关的一般条款。这一民法典草案,不仅在结构体例上与《法国民法典》类似,而且在基本宗旨上也是力图简洁、清晰地涵括全部法律原则。
面对一个渊源多元、构成复杂、甚至存在内在冲突的法律规则体,纽约州法典起草委员会虽肩负重大使命,但仍然需要有一些可据以遵循的法典编纂原则,指导具体的筛选、编排、起草等工作。对此,根据菲尔德的报告:
他们[纽约州法典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尽量选择那些为我们的法律所熟知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当前的环境并且应该可以持续适用的一般规则。他们相信,他们在编排这些规则时采用的方法会得到精研科学的学者的认可,同时还会帮助律师和公民更容易地——如果不是更深入地——认识法律。他们自己认为,就那些将来注定出现、却无法预见的案件而言,总是需要有一般原则、解释规则及类比,来指导司法判决。
可见,当时的法典起草委员会所遵循的法典编制原则包括:①已经被美国当时的既有法律所熟知,②在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以适用,③并且可以持续适用。
在具有普通法传统的现代国家,是否编制一部法典,实际上是一个在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之间的选择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是英美法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争辩之一。通常认为,如果法律是应得到遵守的,就该众所周知;如果法律是应众所周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编制并公布法典。在有些国家,如果不同的法令之间存在冲突,那么,仅仅用成文法方式界定相关权利,就会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也就不可能尝试制定成文法或者编制法典。然而,在菲尔德看来,这些理由并不适合19世纪中期的美国,特别是纽约州:
在纽约州,既没有不同的法令,也不存在相互冲突的社会阶层。人民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样的意志恰好适合用成文宪法和成文法律予以表达。事实上,看起来[除了创制成文法典之外]再没有其他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了。
实际上,该委员会的使命能否完成,能否将“整个法律体系”简化为一部或几部法典,或者最终徒劳无功,这一问题无论在美利坚还是在英格兰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论。
为了支持上述观点,菲尔德尝试比较异域法律的经验与成就。例如,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很难简化成一部法典。事实上,它依然得以简化,虽然引起了当时许多法律人的反感和忧虑,但经过时间的检验,世人已经认识到《优士丁尼法典》对整个人类的伟大贡献。又如,法国自大革命伊始,就同时适用罗马法和当地的习惯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典体系为整个法国建构起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不仅替代了以前的法律,还为欧洲大陆塑造了一个法典编制的典范。因此,制定这样一部法典,是无需争辩的。
实际上,自1847年加入纽约州法典起草委员会伊始,菲尔德便成为美国19世纪法典化运动的“心脏和灵魂”。菲尔德及其主导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不仅编制了五部法典,从整体上建构起一套堪与法国媲美的完整法典体系,而且还从概念、逻辑上对法条的语词、句式进行了严谨细致的琢磨筛选。因此,19世纪纽约州法典体系注定成为20世纪美国法典化运动的“精神之父”。无论自身的成败,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关于这场“法典化”运动和菲尔德引领的法律改革派的尝试,都引起了后来法学家或思想家的认真对待和激烈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