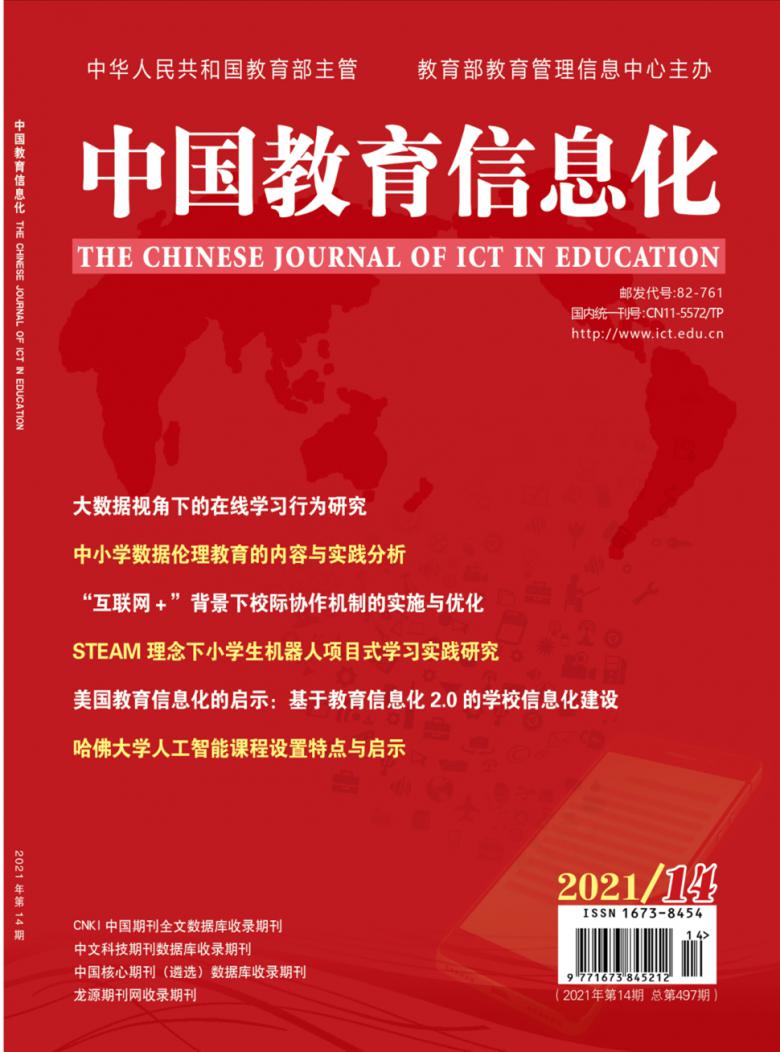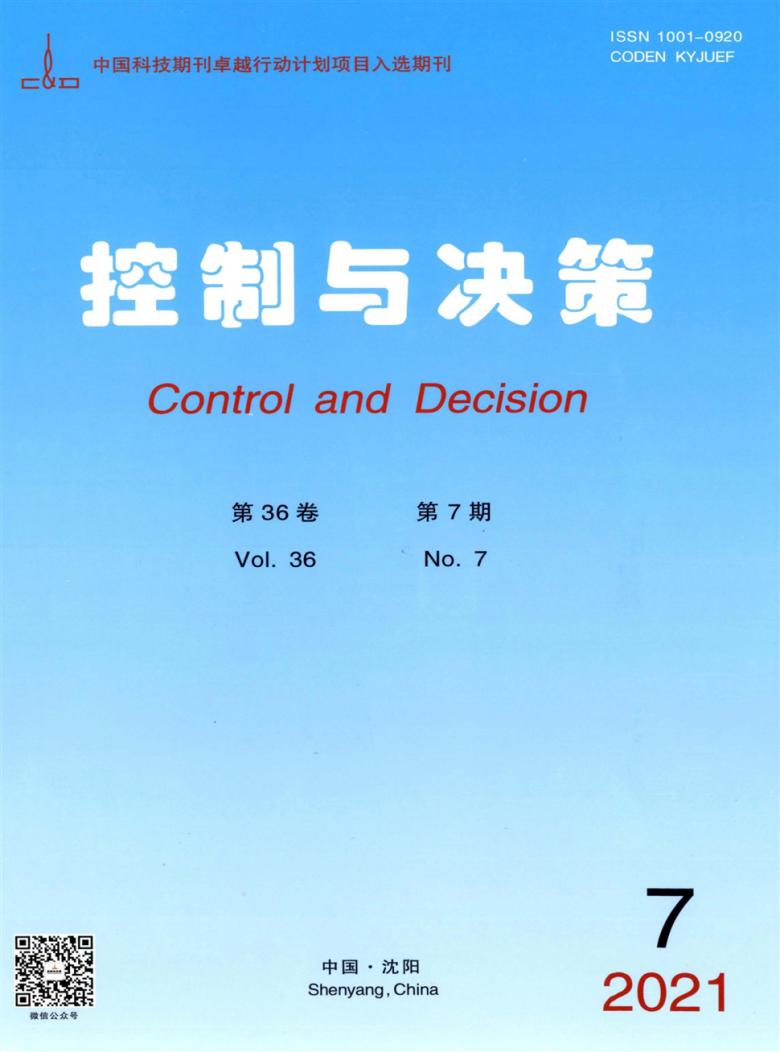摘要:《民法总则》实施后,商事习惯在我国具有两类功能:一是解释意思表示、解释和补充合同;二是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而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司法实践就已将商事习惯作为法源,并且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功能。未来法院在适用时应注意对商事习惯的审查,包括合法性、合公序良俗的形式审查和合理性、可预见性的实质审查。在作为解释和补充合同的工具时,不得用商事习惯否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只有在作为法律渊源时,商事习惯才能修正合同条款。商事习惯在发挥解释和补充合同的功能时,应作为事实问题,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发挥法源功能时,法院可依职权援引商事习惯裁判。但是法院适用商事习惯存在交叉引用的问题,法院应明确其法律依据,以适用不同的解释规则。
关键词:商事习惯,司法功能,审查,修正合同,法律性质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总则》第142条延续了此前《合同法》第60、61、125条的立法意旨,将习惯引入意思表示的解释。《民法总则》第10条同时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如此“习惯”在我国就有了两种法律功能:一是解释意思表示、解释和补充合同;二是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在民商合一大背景下,商事习惯自然也涵盖其中。但是,商事习惯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间是否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后是否会继续存在?该如何解决?
国内对于商事习惯司法功能的研究并不多见。艾围利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商事习惯在司法适用中可以作为裁判依据、证据和纠纷解决办法,周林彬教授、王佩佩博士认为其具有混合作用,对交易行为既有解释性又有补充性作用,在商事纠纷中更有证据之功用。但在效果上,他们认为,商事惯例在我国司法审判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法院对其适用非常少。作为说理手段的多,作为判决依据和证据的少。民事习惯运用的多,商事惯例运用的少。综上,现有研究要么将其作用限定在合同法领域,要么浅尝辄止、对商事习惯的司法功能未予展开,有些观点尚需进一步检验。
由于《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并无关于商事习惯的具体规范,法院在提及商事习惯时使用的词汇也各有不同,包括商事习惯、商业习惯、商事惯例、商业惯例,若从学理上仔细纠察,可发现习惯与惯例有所差异,但就本文的研究对象——法院裁判文书而言,并未对上述概念加以区分。交易习惯则未必等于商事习惯,从外延来看,其范畴大于商事习惯,还可能存有不具有商事色彩的交易习惯,但无论是从商法理论上还是商事司法实务上,交易习惯大多存在于商事领域,对其区分也无必要。因此,在援引法院判决时以上各词可能会交替使用。样本选取方面,本文以北大法宝数据库为案例来源,以成文法确定的“交易习惯”为关键词,随机选取122宗案例,作为本文论述的统计基础。
二、商事习惯司法功能的实证考察
《民法总则》颁布以前,尽管成文法上并未将商事习惯规定为法律渊源,但《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为法院将商事习惯引入裁判提供了渠道,一些程序法规则也为法院援引商事习惯提供了切口,所以法院在适用商事习惯断案上并未受到过多掣肘,反而十分积极。按法院援引商事习惯意在解决问题的部门法划分,可将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分为实体法功能和程序法功能。所谓实体法功能是指法院用商事习惯确定案件裁判所需要的规则,具体包括法律、合同和公司章程三个方面。所谓程序法功能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用商事习惯来解决一些事实判断上的问题,如举证责任分配、事实认定和证据评价等。
(一)实体法功能
法院在处理纠纷时需要确定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规则,常见的规则包括法律和合同,商事纠纷中的规则还包括商事主体的自治规则,即公司章程,法院在解释和补充规则时会用到商事习惯。
1.解释和补充合同
商事习惯能够解释合同,《合同法》第61条、第125条对此定有明文,这为法院将商事习惯引入司法活动铺平了道路,也赋予了学理上关注商事习惯的契机,甚至有学者将其上升为合同解释的原则对待,称为参照习惯(custom)与惯例(usage)原则。当然,通行的观点将其作为解释合同的方法来看待。我国学者韩世远教授在提到合同解释时将其分为狭义的合同解释、补充的解释和修正的解释。狭义的合同解释是指确定当事人赋予其表示行为的含义。补充的解释是指对当事人的表示未尽之部分,未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法官须补充合同的内容。修正的解释是指如按当事人的表示的原样赋予法律效果,则会有悖事理的场合,法官不能不对合同的内容予以修正。下面就将从狭义的解释、补充的解释和修正的解释三个方面论述商事习惯在合同解释中所起到的功能。
(1)解释合同条款
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将商事习惯用来确定合同主体、确定合同的成立与否、判断合同效力、计算或调整违约金、确定具体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判断合同义务性质即合同义务究竟为主给付义务还是从给付义务。用商事习惯解释合同最为常见,在样本选取中所占比例也较大。因这一现象较为平常,其间蕴含的问题并不突出,在此不予详述。
(2)补充合同漏洞
合同不可避免地有漏洞,其中一些漏洞要靠习惯来填补。我国《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这是用商事习惯补充合同漏洞的正式法律依据。习惯在广为应用的商事技术上承担了补充漏洞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活动中还用商事习惯来确定“不确定合同概念”,例如,(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2635号判决中,争议问题在于“合理期间”的计算,法院认为,截至两公司起诉之日,应视为瑞恩公司与两公司在合理期间内协商不成,以两公司的起诉之日即2011年3月31日作为造成增资款资金占用损失的起算点较为合理,亦不违背相应的商事惯例及交易模式。此为用商事惯例确定了“合理期间”。
(3)修正合同
用商事习惯来解释合同和补充合同可谓共识,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现象是用商事习惯来修正合同内容,即所谓修正的解释。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合同明示的内容明显违背商事习惯,则会用商事习惯来否定合同条款。
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合同中约定支付方式是转账,法院认为,无论是现金还是转账,均符合商业惯例,付款存在承兑汇票支付方式,而非严格依据合同采用转账的方式进行,不是对合同的违背。如果说本案只是扩张了合同所谓支付方式的范畴,表现为目的性扩张的话,下面一个案例则直接否定了合同的内容,(201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54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民然公司主张支付对价的事项是《统购铝料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但该合同约定有违一般商事交易惯例,而且,民然公司取得案涉支票所给付的对价亦不属合理范畴。其二,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履行期长达5年,但约定了10个月内预付与案涉关联的4张支票相当的金额,而且民然公司仅需保证统购期限(即合同履行期5年)内销售予康福尔公司的铝料总价不低于前述的预付款850万元。上述权利义务的约定明显有违商事惯例。”继而,法院完全否定了合同条款的效力,而根据掌握的商事习惯确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可以说,用商事习惯修正合同十分危险,推翻当事人的意思而将法院所认为的商事习惯施加给当事人,是对意思自治的极大破坏,也突破了《合同法》的规定,在《民法总则》没有将习惯作为法源之前,这一做法合法性存在问题,具体分析容后详述。
2.解释公司章程
除了解释法律和解释合同以外,还可以发现用商事习惯解释公司章程的案例。公司章程没有法律的普遍性,也没有合同那么严格的相对性,其作为自治规则能约束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从法官活动的角度而言,对公司章程的意义发现仍属确定规则的范畴。当争议各方就章程条款的意义发生争议时,法院也会借助商事习惯确定公司章程的内容。该类案例仅有一例,占样本的0.9%。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黑监民再字第86号民事判决中,争议问题在于对英文“directors”的理解,法院认为,就本案争议的公司章程第18条所规定的内容而言,其各项权力亦应由董事会行使更符合公司运营常理及一般商业惯例。由此可见,“directors”一词在该《公司章程》中译为“董事会”更符合用语本意及行文一致,将“Powers of Directors”译为“董事会的权力”更为准确。此案发生时,用商事习惯解释公司章程并无法律依据,如今《民法总则》第10条可作为解释章程的依据。
3.解释法律
虽然并无法律的规定或授权,但是法院在确定法律含义时,商事习惯也会发挥作用。一则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确定先合同义务,应结合案中拟订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进行认定。此案中,争议的问题乃是先合同义务的内容,法院无法援引《合同法》第60条和第6l条,在缺少了这一媒介情况下,商事习惯直接作用于法律的解释。
法院用商事习惯来解释法律的现象并不多见,具体数量及比例如上表所示。原因在于,用商事习惯来解释合同有着明确的法律授权,而用其解释法律则需要法院的勇气。需要指出的是,《民法总则》颁布之前,习惯尚不能发挥弥补法律漏洞的功能,经过搜寻也未能发现此类案例,有学者将其归因于法官的职责和规避风险本能。除此之外,技术上而言,凡法院裁判的纠纷,若需动用商事习惯,则应发生在商人之间,通常即为合同纠纷,法院大可借补充合同漏洞之名完成规则之确定,无需以补充法律漏洞之名进行。但是《民法总则》将习惯确立为法律渊源,则赋予了商事习惯补充法律漏洞的功能,运用商事习惯补充法律漏洞于法有据,只是如何具体操作有待研究。
(二)程序法功能
教义学上来讲,商事习惯属于经验法则的一种,作为事实判断因素而存在。在审理案件中,法官也要运用经验法则进行裁判。通过案例整理可以发现,商事习惯主要在举证责任分配、事实推定、证据评价方面被司法机关所利用。商事习惯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作用不限于合同案件,侵权案件、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案件中法院也依据商事习惯判断案件事实。此外,商事习惯还被用来确定损失的数额。以下只讨论商事习惯在程序法上的主要功能。
1.决定举证责任分配
(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12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本院根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的约定以及商事惯例,推定两名被上诉人的陈述缺乏真实性,而两名上诉人的陈述更符合常理。即包括共同经营期间内的营业额等在内的公司财务材料,更应当由股权受让方即两被上诉人来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由此,对于共同经营期间的损失一节因举证不能而事实不清的不利后果,更应由两被上诉人着重承担。然而法院的这种做法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裁判文书的行文中亦未标明其法律依据为何,这可能也是商事习惯此类功能在样本中所占比例较低的一个原因。比较接近的规范依据似乎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法院在此援引商事习惯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根据,应当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这反映了法院在运用二原则时的谨慎态度,即将较为抽象的公平和诚实信用,落实到较为具体的商事习惯,以此来确定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承担,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抽象原则的不确定性,也为自己的分配活动寻找了更为切实的理由,有利于当事人接受。但是,问题也是明显的,法院并未论证所谓的商事惯例具体指什么,为什么根据商事惯例就应当由两被上诉人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其间的逻辑关联是什么,表现出司法运用商事习惯分配举证责任的随意性。
2.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是法官在进行事实认定推理时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构建推理前提以便推出需要认定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3条及《证据规定》第9条均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然,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有学者将其进一步区分为事态推定与行为推定等。严格意义上来讲,事实认定是目标,事实推定是手段。商事习惯应当作为事实推定的初始根据来使用。但在法院裁判文书中,并未严格区分事实推定与事实认定。司法机关在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商事习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有时被用来确认合同是否履行的事实,有时被用来确认侵权事实的存在。
商业习惯在事实推定上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功能,即法院依据商事习惯推定相应的事实存在或否定相应事实的存在。当事人的主张符合商业习惯时,法院依据经验法则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直接推定相应事实的存在;反之,法院认为当事人的主张不符合商事习惯时,会直接否定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存在,而无需对方反证证明。
3.评价证据
从司法实践来看,法律直接规定证据证明力有无和大小的情况并不多,多数情况下仍然需要靠审判人员的判断,即要求审判员按照良知、理性、经验规则对证据证明力有无和大小进行判断《证据规定》第64条、《民诉法解释》第105条均有相关规定。《证据规定》66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在综合审查时,法官可以运用经验法则、逻辑推理等这一环节中,法院用商事习惯来确定证据的证明力,商事习惯依然充当着日常生活经验的角色。
依据商事习惯进行证据评价,与事实认定一样,也有着积极评价与消极评价两种,即根据商事习惯认可证据的证明力和否定证据的证明力。认可证据证明力时,法院常常表述为“符合商事习惯”;否定证据证明力时,法院常常表述为“不符合商业惯例”,“有违正常的商事习惯”,“有悖于一般的商事习惯”,“与通常商事惯例不符,本院难以采信”,“明显违背商业习惯和商业常理”等。
商事习惯在法院发现事实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作用,这点被商法学者所忽视。诉讼法学者将其作为经验法则的一种偶有提及,但着墨寥寥。实则商事习惯不仅帮助法官规定规则,更助力法官发现事实,其程序法功能在全部样本中占到了接近半数的比例。若对后者视而不见,而归入法院说理过程,似抹煞了商事习惯的部分功能。
通过以上对我国法院裁判的观察发现,尽管以前立法上并未承认商事习惯的法源地位,法院援引商事习惯判案却十分积极。在规则确定中法院借助商事习惯解释法律、解释和补充合同及解释章程实现了将商事习惯引入规则的结果。在事实发现中,法院借助经验法则实现着商事习惯在事实认定和证据评价中的功能,借助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实现着商事习惯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影响。但其中的问题颇为令人担忧,适用商事习惯的112件案例中,无任何一个裁判中对于所引用的商事习惯进行内容上的说明,即其所援引的商事习惯所确立的原则、规则或经验法则是什么样的,裁判行文中只有“根据商事习惯”、“符合/违背商事习惯”的表述,似乎商事习惯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随意性。在习惯尚未成为法律渊源时尚且如此,《民法总则》适用过程中商事习惯的随意性问题只会更加突出,亟待规范。
(三)适用阻碍
研究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不能仅看成功案例,还需关注失败案例以发现问题。在122件样本中,当事人主张适用商事习惯的为24件,其余为法院自行援引商事习惯断案。在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中,并未全部成功。
其中有9件案例中法院否定了商事习惯的适用,即目前样本中当事人主张商事习惯的失败率为37.5%。当事人主张并被法院支持的有15件,当事人的成功率为62.5%,成功率过半。在失败的原因方面,包括了未完成举证责任、不能用商事习惯否定证据和商事习惯与合同条款有悖。
通过上述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情形来看,法院在两个意义上适用商事习惯,一是解释和补充合同,另一个则是作为确定的规则调整合同,发现事实。后者中法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商事习惯作为法律渊源,直接引用以裁判案件。同时,法院在适用或拒绝适用商事习惯方面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否定当事人主张的理由恰恰与上述商事习惯的实际作用相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合同条款不一致的商事习惯能否适用?换句话说,能否用商事习惯修正合同?二是能否用商事习惯否定证据,证据与商事习惯发生冲突时以何为准?三是商事习惯的适用是否需要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能否用商事习惯否定证据主要涉及商事习惯在证据法上的定位问题,限于篇幅及专业,在此不予讨论,结合上文提到的法院适用商事习惯的随意性,接下来从三个方面分析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商事习惯的适格性、商事习惯与合同条款的关系、商事习惯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