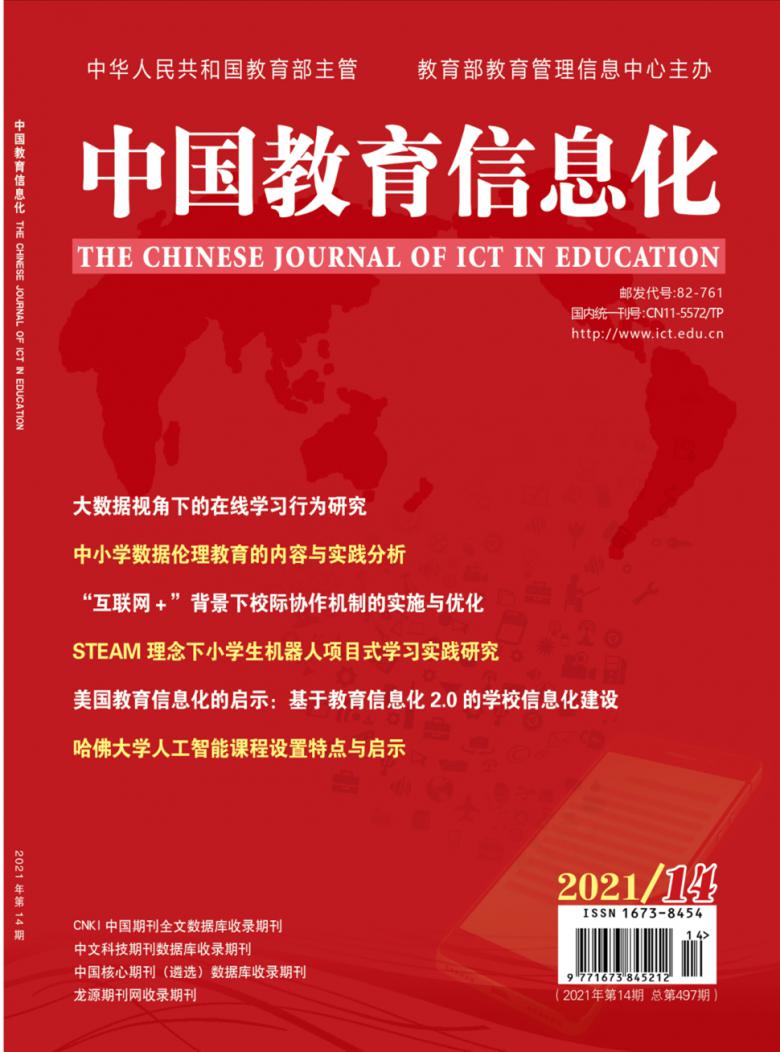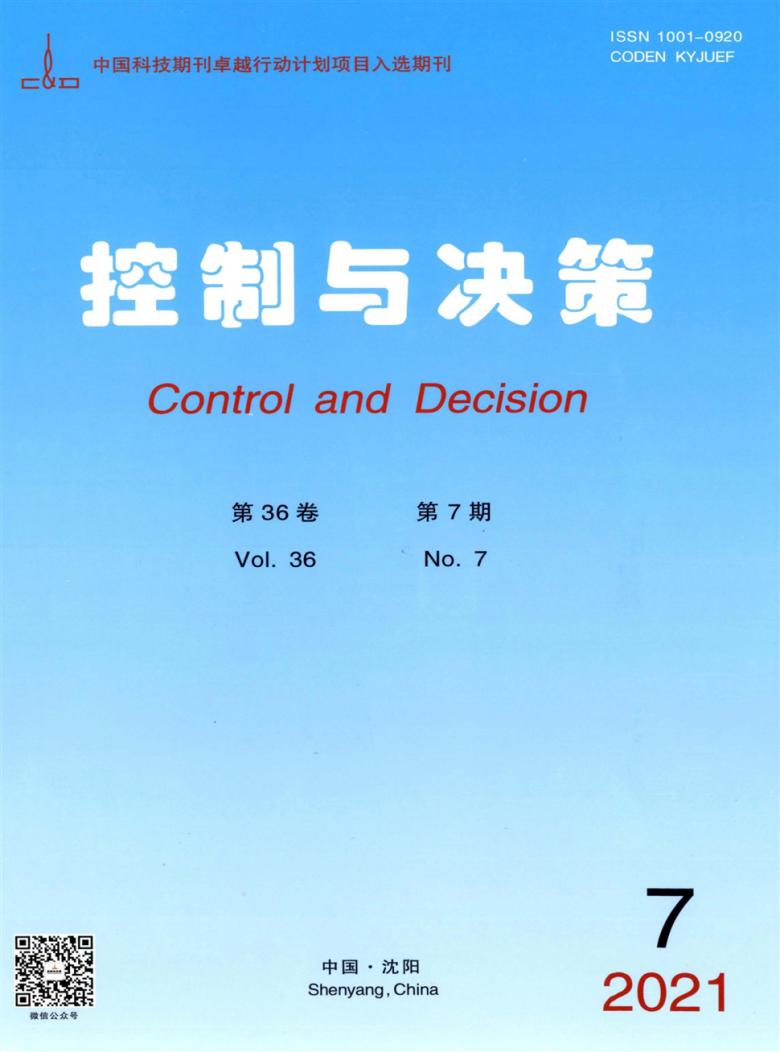摘要:考察涉及虚假诉讼的裁判文书可见,目前对虚假诉讼的确认以再审为主,检察监督作用突出,虚假诉讼的识别存在滞后性,且多数裁判仅驳回诉讼请求,罚款或拘留等强制措施适用率低,对虚假诉讼的惩治有限。为改变上述局面,可通过惩戒虚假陈述间接规制虚假诉讼,同时放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参诉条件,赋予主张本诉涉嫌虚假诉讼可能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案外人参加诉讼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在规制手段上,应加强对虚假诉讼的审查,加大民事制裁的力度,并允许利害关系人提起侵权之诉,以构建在民事诉讼程序内多元化的虚假诉讼规制体系。
关键词: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第三人撤销之诉,虚假陈述
目前,我国虚假诉讼呈蔓延趋势,不仅严重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本文通过考察确认为虚假诉讼的裁判文书发现,当前对虚假诉讼的识别与规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检察监督成为启动再审进而确认虚假诉讼的主要途径,其中以法院的刑事判决为依据进而确认虚假诉讼的亦不在少数。欲有效遏制虚假诉讼,需要激活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机能,赋予利害关系人启动相关程序的权利,以及时识别和规制虚假诉讼,并减少其中司法资源的浪费。
一、虚假诉讼的识别与规制:实践表达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虚假诉讼”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涉及39721个案件,其中有269个案件被确认为虚假诉讼。对这269个案件的裁判文书予以整理,可发现识别与规制虚假诉讼存在以下规律:
第一, 再审成为确认虚假诉讼的主要程序。在269个确认为虚假诉讼的案件中,有231个案件通过再审程序确认,所占比例为85.87%;有5个案件通过二审程序确认,占比为1.86%;有32个案件通过一审程序确认,占比为11.90%;还有1个案件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确认,占比为0.37%。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近九成涉及虚假诉讼案件到了再审程序才得以确认。
第二, 检察监督成为启动再审进而确认虚假诉讼的主要途径。在通过再审确认虚假诉讼的231个案件中,从启动再审的方式上看,检察监督启动再审的有146件,包括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两种方式;案外人或原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有32件;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有53件。从中可见,半数以上的再审案件通过检察监督得以启动,并进而确认为虚假诉讼。此外,在再审程序中,往往法院先前的刑事判决成为认定虚假诉讼的主要依据。
案例一:赵伟龙、程梅因其借贷纠纷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为稀释案外人的执行份额,二人串通柳锦霞进行虚假诉讼,并在一审中通过调解方式结案。之后其虚假诉讼的行为被检察机关察觉,赵伟龙被认定构成妨碍作证罪。刑事判决作出后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民事抗诉,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案件为虚假诉讼,撤销调解书,驳回柳锦霞的诉讼请求。在这一案件中,法院的刑事判决成为认定虚假诉讼的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诸如案例一以法院的刑事判决为依据确认虚假诉讼的并不罕见。通常而言,检察机关在获得虚假诉讼的案件线索之后,往往会对案件进行详细的调查,在确认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下才会提起刑事公诉,或者提起民事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检察监督对于虚假诉讼的识别与规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 案外人的申诉和申请再审成为发现虚假诉讼的主要线索。如前文所述,检察监督成为启动再审的主要途径,而检察监督的主要线索源于案外人的申诉或举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就曾表示,对虚假诉讼的监督,检察机关一般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外人控告举报启动监督程序。此外,因虚假诉讼申请再审的主体中,案外人亦占绝大多数。前述当事人或案外人因虚假诉讼申请再审的32个案件中,有28个案件为案外人申请再审。可见,发现虚假诉讼的主要线索源于利益受到损害的案外人。
案例二:顾金清向法院诉称,杨鹤林因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向其借款40万元,到期拒不还款,要求法院判决归还40万元借款。后双方经调解达成协议,杨鹤林以其所有的设备作价30万元用于清偿借款,并支付剩余10万元欠款。之后,案外人沈永良向检察院提出申诉,检察院提起抗诉,法院经再审确认原审案件系虚假诉讼。
案例三:王兴林向法院诉称,通达煤矿向其借款800万元,并约定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且款项已支付到第三人工行账上,但通达煤矿未归还欠款,故请求还款。通达煤矿对王兴林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可。案外人李志勇提出原被告双方的债权债务系伪造,目的是为了对抗法院案件的执行。因案外人提出异议,法院要求原被告就借款事实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双方未能提供。最后经法院调查,确认案件为虚假诉讼。
案外人作为虚假诉讼的受害方,其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显然更为关心,在申请再审无果后,往往会选择向检察院申诉寻求救济,这也间接成为识别与规制虚假诉讼的关键。而在一审程序或者二审程序中被确认为虚假诉讼的案件,也有部分案件是由于案外人作为第三人参与才使得法院及时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并对虚假诉讼予以规制。
第四, 对虚假诉讼的规制以驳回诉讼请求为主。在269例确认为虚假诉讼的案件中,对虚假诉讼的处理主要为驳回诉讼请求,采取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仅有8件,且多为罚款。
案例四:周艳丽与王玉章原为夫妻,二人婚后共同购买了房屋,2009年王玉章死亡。周艳丽与其男友王永生未经王玉章的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授权擅自出售了周艳丽与王玉章名下的房屋,并与陈中奇共谋伪造借条,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转让房屋。之后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案件为虚假诉讼,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四中,当事人双方通过虚构借款事实,伪造借条的方式骗取法院裁判,并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不仅损害了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也扰乱了司法秩序和房地产市场秩序。但是法官并未对虚假诉讼行为人予以制裁,仅仅驳回诉讼请求。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对虚假诉讼案件的通常处理方式,即仅驳回诉讼请求,并不对其实施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五, 对虚假诉讼予以刑事制裁的比例远远大于民事制裁,且对于涉及犯罪的虚假诉讼行为,往往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在269份确认为虚假诉讼的司法裁判中,标明已受刑事制裁的有65件。受刑事制裁的案件数量为民事制裁的7倍之多,并且65个案件均为行为人在受到刑事制裁后才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确认虚假诉讼。
案例五:陈宝兴、陈春国于2011年共同向戴素娟借款150万元,宝恒公司、戴绍对该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戴素娟、陈宝兴经事先商量,在陈宝兴名下宝恒公司拆迁补偿款不足以偿还全部债权人借款的情况下,为让戴素娟多分配执行款,虚增戴素娟借给陈宝兴、陈春国父子借款人民币197万余元,由戴素娟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获得了原审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并以此参与分配执行款,使得戴素娟多分配到人民币44万余元。之后,其虚假诉讼的行为被发现,法院于2016年10月作出刑事判决,认定戴素娟和陈宝兴均构成虚假诉讼罪。2016年12月案件被检察院提起抗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撤销原判,驳回戴素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于虚假诉讼行为构成犯罪的,多数案件采取诸如案例五的方式,先对虚假诉讼行为人予以刑事制裁,之后再通过民事再审撤销原判,驳回诉讼请求。通常情况下,刑事制裁与民事制裁仅选择一项适用,在65件涉及刑事制裁的案件中,仅有1件同时对虚假诉讼行为人进行了民事制裁。
此外,考察确认为虚假诉讼的裁判文书发现,原审案件以调解结案的有179件,以判决结案的有53件,调解成为虚假诉讼首选的结案方式。而对案由的观察还发现,共有175份裁判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90份为合同纠纷。可见,虚假诉讼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类型。至于虚假诉讼的目的,则包括侵吞他人财产、逃避债务、稀释债务以获得受偿款、规避房屋过户税款以及其他逃避法律法规的目的等。
二、虚假诉讼的识别与规制:问题与成因
通过对涉及虚假诉讼案件裁判文书的考察,发现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对虚假诉讼的识别与规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识别与规制虚假诉讼的滞后性。如前所述,近九成的虚假诉讼案件到了再审程序才得以确认。此时即使确认为虚假诉讼并予以规制,有的已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或者即使利害关系人的损失得以弥补,也已经影响了市场秩序的稳定性和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案例六:徐彩霞向法院诉称,其借给薛春晨30000元,借期1个月。借期届满后薛春晨未能还款。后经法院调解,徐彩霞提出可以把其住房公积金取出归还借款,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法院制作了调解书。后徐彩霞凭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在扣划执行费后,将薛春晨公积金账户上的27350元划归徐彩霞。后经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确认原审案件为虚假诉讼,判决撤销调解书,驳回徐彩霞的诉讼请求。
上述案件虽经查证后,原调解书被撤销,但其行为本身已造成对国家经济管理秩序和市场秩序的损害。因此,如果对于虚假诉讼行为仅能通过再审程序进行事后规制,不能在发现之初及时予以处理,则无疑加大了处罚成本,难以起到规制效果。
二是对虚假诉讼的民事规制力度小。实践中对虚假诉讼的民事规制主要是驳回诉讼请求,适用罚款的案例不多,拘留更为少见。即便是罚款,罚款的金额多为诉讼标的额的5%以内,制裁力度有限。
案例七:张雪华向法院诉称,张淑芳因资金短缺向其借款人民币30万元,但并未按期归还,要求张淑芳及其丈夫张俊彬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张俊彬辩称原被告之间的借贷不真实,系虚假诉讼。后经法院查明案件确为虚假诉讼,目的是为了在以后的离婚诉讼中获得不当利益,后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对二人分别罚款1万元。相对于30万的诉讼标的额而言,单人的罚款数额不足诉讼标的额的4%。
对于虚假诉讼的行为人而言,虚假诉讼本身具有隐蔽性,难以察觉,即使在民事诉讼中被发现,如果不被处罚或者受到极小的处罚,与其可能获得的利益相比微不足道,行为人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虚假诉讼也就成为“理智”的选择。
而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虚假诉讼的认定标准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9条的规定,虚假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之所以提高虚假诉讼的证明标准,来自司法解释起草者的解说认为,参考域外相关立法,许多国家对民事欺诈或者可能涉及刑事行为的民事案件的主张均要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加以证明,且我国民事实体法也要求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提高证明标准,故将虚假诉讼的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以构建层次性、多元化的证明标准体系。当然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说明亦指出,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非完全一致,其并非要求待证事实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存在。且民事诉讼不像刑事诉讼事关个人的自由与生命,即使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也要衡量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不能过分僵硬地适用。但即使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低于刑事案件,其仍然高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司法实务中,即便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下,恶意串通行为的受害人仍然很难证明恶意串通事实的存在。而要求民事法官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与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形成有效区分,在很多法官运用证明标准凭感觉、经验以及判决书论证不足的背景下,存在困难。实践中虚假诉讼多存在双方当事人的恶意串通行为,其本身就具有秘密性,民事诉讼程序缺少公安机关的介入,难以通过侦查手段获得有力证据。仅仅依靠法官自身或者受害人来查证虚假诉讼,无疑增添了难度,也因此抑制了制裁虚假诉讼和保护案外人民事权益的机会和力度。因此,部分法官即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了虚假诉讼,也多因难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而对虚假诉讼行为不予认定,自然无从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人予以追究。
二是法官对于虚假诉讼的审查与制裁较为消极。究其原因,一是在民事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重调解的情况,一些法官热衷于调解,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疏忽甚至无视法院的审查义务,有的即使发现案件存在异常,诸如不合理的自认或者和解行为等,也听之任之,对异常之处不予追查。二是我国法院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而对虚假诉讼予以详细调查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无疑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繁重的办案压力和严格的审限制约下,法官即使发现案件涉及虚假诉讼,通常也选择驳回诉讼请求了结,而对虚假诉讼事实不予认定;三是虚假诉讼案件多缺乏案外人的参与,常常是在诉讼程序结束后通过特殊的救济途径,因案外人的介入才能得到确认,此时对虚假诉讼行为制裁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司法机关在纠正或撤销虚假诉讼而产生的判决、调解书的同时,忽视了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