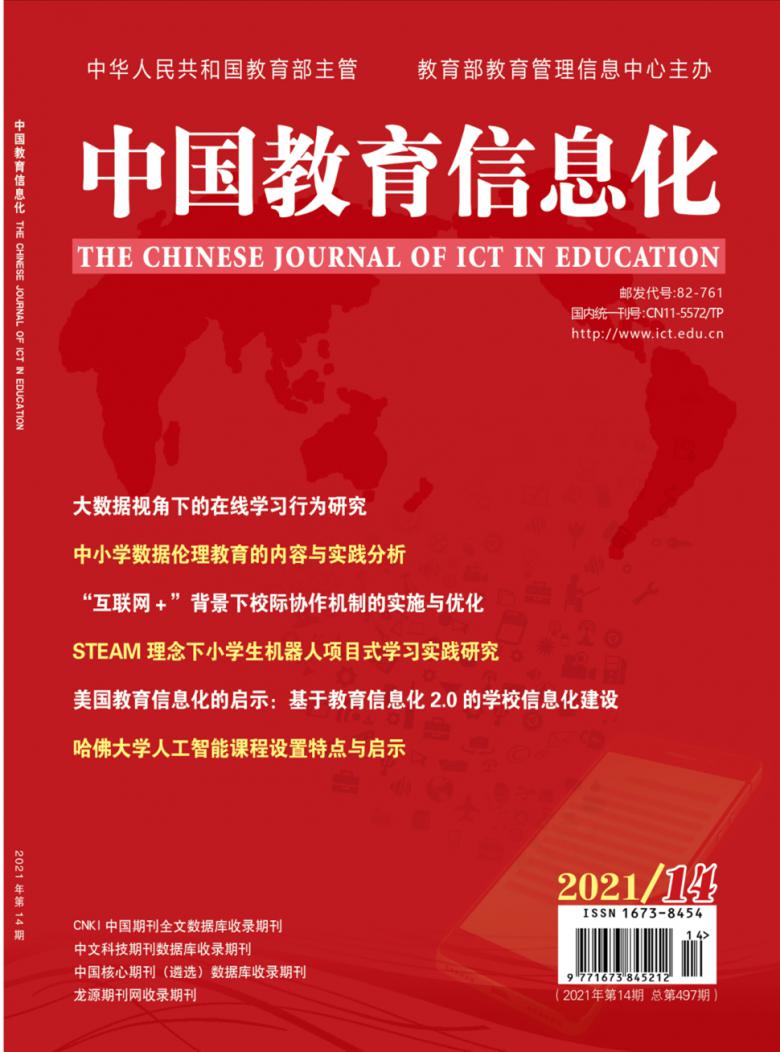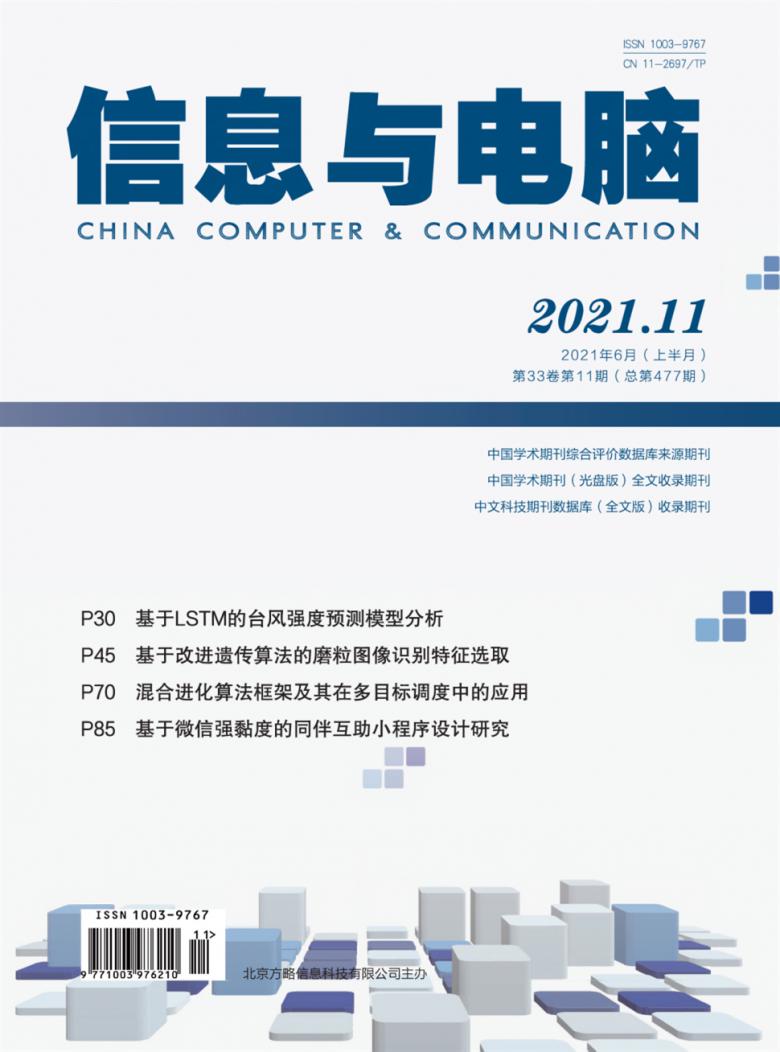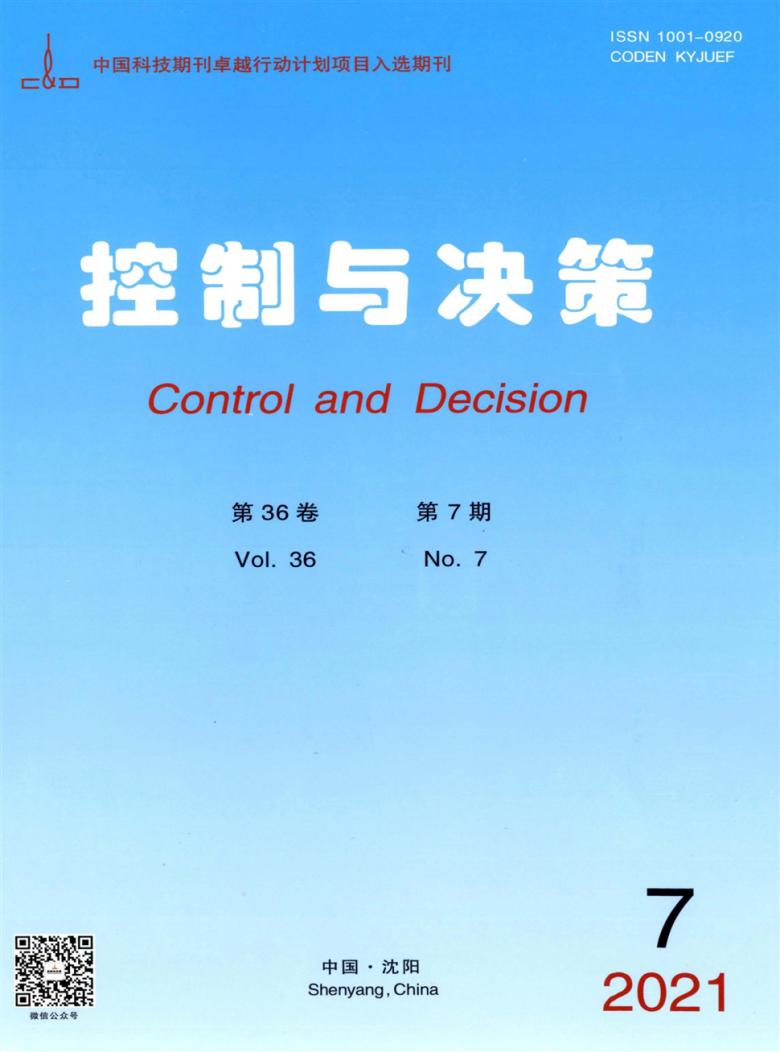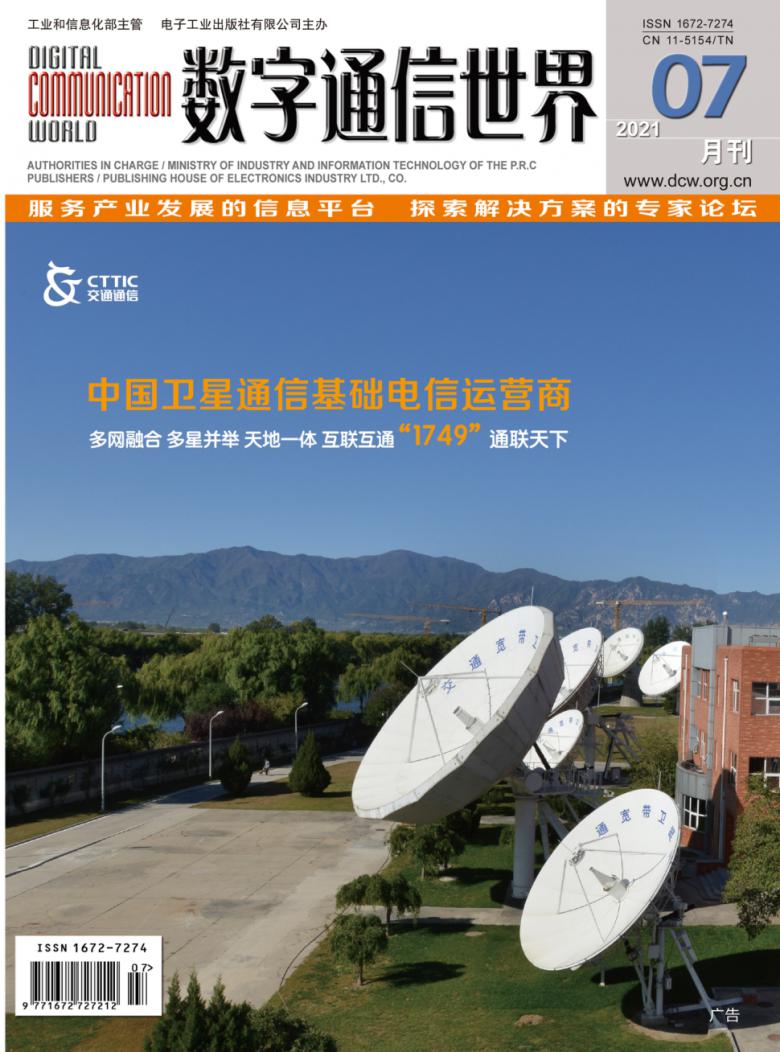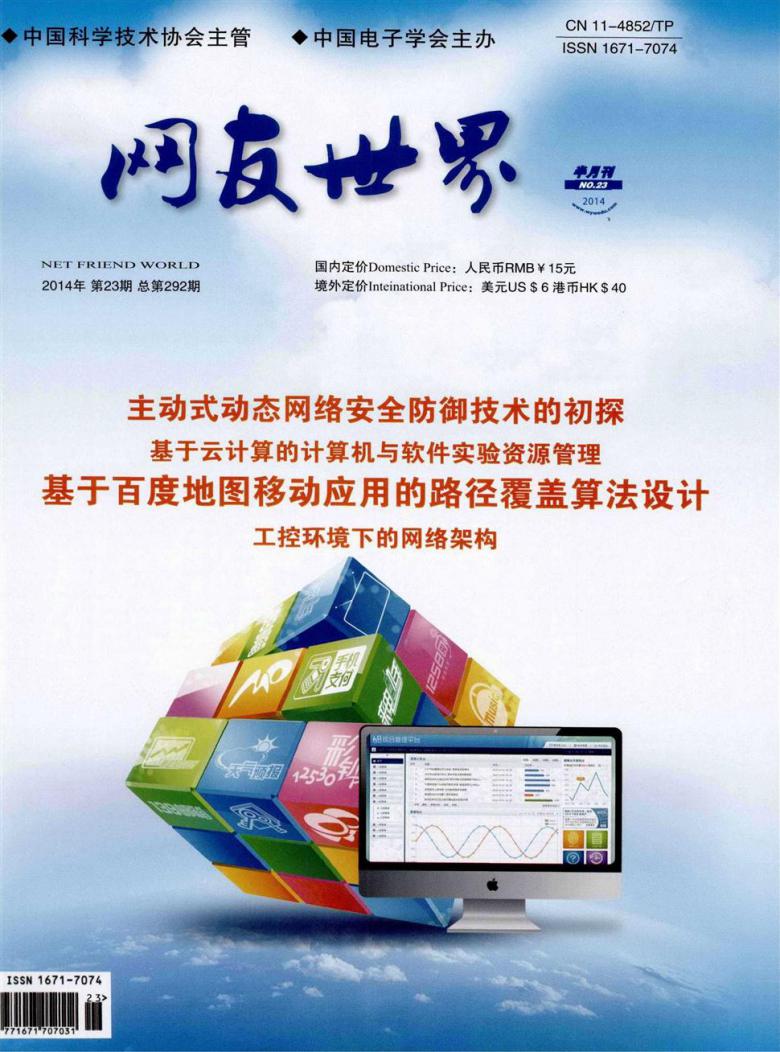摘要: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首要之关键在于深究与厘清农村小规模学校生存的价值基础。二元博弈中的时代性价值基础、特殊存在中的内生性价值基础以及公平诉求中的现实性价值基础构成了农村小规模学校生存价值基础的三大维度。发展好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促进农村教育脱贫攻坚的底部战略武器。
关键词:农村小规模学校,生存的价值基础,教育公平
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基本道路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途径,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劳动力与人口的大量流动,农村多数学龄儿童随父母进城入学。在这种情况之下,城市学校的人数激增、规模扩大,而农村学龄人口则呈不断缩减态势,从而导致越来越多农村地区的学校成为了“小规模学校”。然而近年来,因社会中所出现的撤留博弈,以及博弈背后多元利益主体与多元价值观的差异,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存状态饱受非议。因此,首要之关键在于深究与厘清农村小规模学校生存的价值基础。
一、边缘地带———二元博弈中的时代性价值基础
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一种适应于偏远农村地区,并基于人数较少适龄学生的特殊教育形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均有所差异。在教育朝规模化与效率化方向发展的基本进程之中,农村小规模学校似乎与该发展潮流背道而驰,因此受到了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与经济理性主义的质疑,并被推入了教育发展的边缘地带。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撤与留的这场博弈将农村小规模学校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深度热议之中,博弈的历时性也随社会的变迁与政策的更替出台而不断持续。
如若将这场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简言之,即为撤点并校时代与“后撤点并校”时代。自2001 年以来,以规模和效益为重点的撤点并校时代拉开了序幕。然而,在政策实行的过程之中却被一些地方政府“一刀切”,这样对政绩的一味追求使得撤点并校运动逐渐异化,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分歧,造成了农村教育“城挤、乡弱、村空”的现象。“2009~2014 年,乡村小学减少10.54 万所,乡村初中减少1.26 万所,乡村小学在校生减少了2606.68 万人,镇区和城区小学在校生分别增加820.8 万人和1164.48 万人。”由此可见,农村学校在撤点并校时代大幅缩减,农村家庭学龄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此背景之下,农村儿童的辍学率呈反弹趋势,校车事故也频繁发生,撤点并校运动并没有实现预期所要达到的初衷,其实施过程中的盲目性也使得撤点并校演变成为单一的“学校进城”运动。为此,在2012 年8 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同年9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叫停撤点并校运动。自此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重视,我国农村教育进入了“后撤点并校”时代。
具体而言,“后撤点并校”时代是在弥补撤点并校运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其一,分散教学较集中教学而言,其覆盖面更广,更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并将关注点逐渐向社会底层群体倾斜;其二,小规模学校较大规模学校而言,其教学质量更加容易受到保障,如若超出有效管理范围,学生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其三,就近入学较远距离上学而言,学生的安全系数更高,延迟入学与隐性失学等问题的存在率也会更低,将有利于教育实现均衡发展。
撤点并校时代所注重的是教育效率的提高,而后撤点并校时代则是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教育公平,着重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效率与公平实则可以相互促进与转化,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存在正是这一双向过程中的有效法宝,也是减少地区教育差距,从而逐步弱化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有力武器。叫停撤点并校,并振兴农村小规模学校,其过渡的过程中免不了刹车的惯性作用,因此问题的尖锐性与过程的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其政策由最初的合并、消除,转变为保留、扶持小规模学校,这是每一次改革都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而非是改革的道路走错了方向。因此,振兴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大势所趋,是保障底层群体受教育权的有效举措,也是挽救农村教育的根本出路。
农村地理位置的劣势加之交通不便等因素,使得农村小规模学校极具生存性价值。目前,浙江和福建等地区已出台政策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从“小而差”向“小而优”转化,可见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已重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存价值问题,制定政策并投入资源来复兴小规模学校。那么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存在价值更应引起相应的重视。如若将农村小规模学校大力复兴,寄宿制学生便可就近入学,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也可在当地接受最便利的教育。
二、因小而美———特殊存在中的内生性价值基础
农村小规模学校因自身的特殊价值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不可替代性。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而言,分工的作用在于保障社会的凝聚与幸福,维持社会的平衡。小规模学校的生存因其适应于偏远农村地区的特殊性而具有重要价值,并与其他分工形式共同体现社会价值,产生出一种社会的和谐。
从生存状态上来说,农村小规模学校并不是一个过渡状态的存在,更不是一个落后的存在,而是一个不会因社会高速发展与教育现代化而退隐或消失的学校形态。“放眼于世界,无论是在瑞士的雪山顶、澳大利亚的牧场,还是美国的西部,农村和地广人稀的地带都存在着小规模学校,所以这必定不是要消失和落后的形态。”此外,一旦涉及到教育的相关字眼,差异化发展可谓是彰显教育真谛的可靠标准,这似乎已然达成了世界的共识。作为教育发生与进行的关键场所,学校的类型理应呈现多样化来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发展。一个国家对于学校的发展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形式,应根据不同群体的具体情况与实际需求来保证不同群体的权利最大化。农村小规模学校作为学校的发展形态之一,旨在最大化满足农村后20%弱势家庭的教育需求,其自身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教育价值基础。
从生存原因上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承担着全球人口的粮食生产供应功能,就此意义而言农村不会消失,满足农村地区发展教育需求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因其内在合理性也必然不会消亡”。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将公平的存在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的教育公平更加离不开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此外,面对校车事故频发的安全问题与家庭负担加重的现实问题,新一轮的辍学潮就此引发。所以说,不论地理环境、经济因素以及人口分布处于多么恶劣的态势,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存都不应受到价值性质疑。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存价值不仅体现在撤并之后的底部攻坚,还体现在小规模学校独有的教育价值基础,而教育的独特性价值恰恰是因其发展的限制与劣势而得以产生。从发展方向上来说,其要旨有三:
其一,有利于保障较高的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小”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在“大就是好”哲学观影响之下的所谓“小而差”言论并没有什么依据与对照,“小”更具有灵活性,“小”的班级规模更具有提升教育质量的潜力。小规模学校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互动和参与的机会,也为教师实行因材施教的差异化教学制造了有利环境。这一“小”的特征虽似乎与教育的规模化发展相悖,但其因规模人数较少的教学条件恰恰可以为素质教育的实施提供有利环境,从而弥补“教育工厂”所存在的难题。此外,在培养学生责任感、兴趣点以及良好习惯的养成方面,小规模学校都一摒“教育工厂”与规模效益的劣势之所在,是未来学校的发展方向。
其二,有助于实施人性化管理,使教育回归人的尺度,是真正面向生活的教育。以留守儿童居多的农村儿童面临着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双重缺失,这些儿童的弱势不仅体现在对知识的吸收与掌握方面,其心理因素、人际关系等方面是否存在异样也亟待得到重视,爱的给予与情感的关怀成为了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中儿童的另一个教育重点之所在。小规模学校中的教师可有机会关注到每一名学生,人数较少的劣势在这里则转化为家校合作与家访便利的优势,从而帮助农村儿童弥补家庭监护的缺位,形成健康的心理环境。
其三,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传承与发扬农村文明的中心与载体,是文化的一种无形象征。因此,着眼于内生发展,将农村内部作为发展主体是农村小规模学校解决自身运作乏力的特殊性价值基础之所在。小规模学校身处农村地区,看似孤僻的区域却是一个个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在“后撤点并校”时代,乡村学校被赋予了新的文化使命。作为乡村文化生长点与农村社区文化的重要中心,农村小规模学校理应承担起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责任,可因地制宜地开发当地乡土资源,在接受文明文化的同时发展当地传统文化的特色化课程,从而捍卫乡村文化的尊严,改变乡村学校与乡村无关的“悬浮”状态。
三、控辍保学———公平诉求中的现实性价值基础
公平是教育的普遍价值,效率与公平在相互制约的同时相互促进是公平观的最佳状态。作为农村教育的重要支撑,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提高农村儿童文化资本的必然存在,也是保障城乡之间教育功能的公平追求之所在。
农村小规模学校生存的客观背景条件确实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多处于位置偏僻、地形复杂、隔离程度高的发展滞后地区。同时因数量少、分布广,其规模化的发展难以形成,最终导致人口的流动与城镇化教育群体的日益庞大,造成了教育城镇化异化与农村教育的空心化。然而反观教育的本质,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每一个灵魂只要有可塑性与发展的可能性,都不应忽视其对教育的诉求。因此,只要有学生存在的地方必有教育,有教育存在的地方必有学校,农村小规模学校不能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剥夺农村儿童对教育的渴望与权利。
小规模学校在存在的类型上也有所差异。现阶段,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属于生存型发展样态,仍然存在大量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与资金不足等问题。但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学校自身生存的合理性,关键在于将农村小规模学校中所存在的劣势向优势转化,将这一教育形态的效用发挥最大化。如若将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从“生存型”过渡为“发展型”,不仅将促进教育公平的进一步实现,也将通过“扶贫先扶智”的手段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的自身存在即是农村教育公平发展之所在,它的生存价值基础不应在“农村教育城市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不应在资源分配与社会分工的过程中利益缺位,而应是扩大农村教育机会的必要形式,是缩减社会阶层之间鸿沟的必然存在。
学校是巨大的民主发动机。用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农村小规模学校更像是教育嵌入整个社会机制下博弈的产物,而社会结构稳定的关键则指向公平。相较于形式公平,实质公平则愈加受到关注与重视,所谓的“起点平等”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平等。对于农村后20%的家庭来说,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依靠教育。在撤点并校的过程之中,处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是这场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他们面对的是家庭贫困与学校资源匮乏的“双重叠加”。如若因所处地区的劣势使得社会最底层人群走不出去的话,不公平感将会抹杀能者的积极性,“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就会不断上演。久而久之,教育没有了希望,“读书无用论”的谬误思想盛行,贫困的代际传递将陷入不可挽回的怪圈。
对于如何才能保证弱势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公平问题,农村儿童的现实性境遇也应受到关注与重视。乡村儿童没有独属于自己的学习环境,究其原因是现实生活所迫。除了经济活动的压力之外,一些隔代抚养下留守儿童的生活压力也是他们缺席课堂以致最终辍学的原因之一。留守儿童必须从小面对家庭的责任,家庭条件的不具备导致一部分农村儿童无法保证每日按时到校上学。如若不重视农村儿童上学的背景条件,不积极创造人类平等的后天教育基础,那么贤能主义的筛选机制就只是在外部世界掩盖了内在不平等,其实质已经背离了公平的诉求。
面对这些渴望上学、渴望知识的孩子们,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存正是满足他们公平诉求、控制辍学率并保证他们基本上学权利的重要举措。迫于经济活动与生活的压力,农村儿童就近上学即是教育公平的最大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