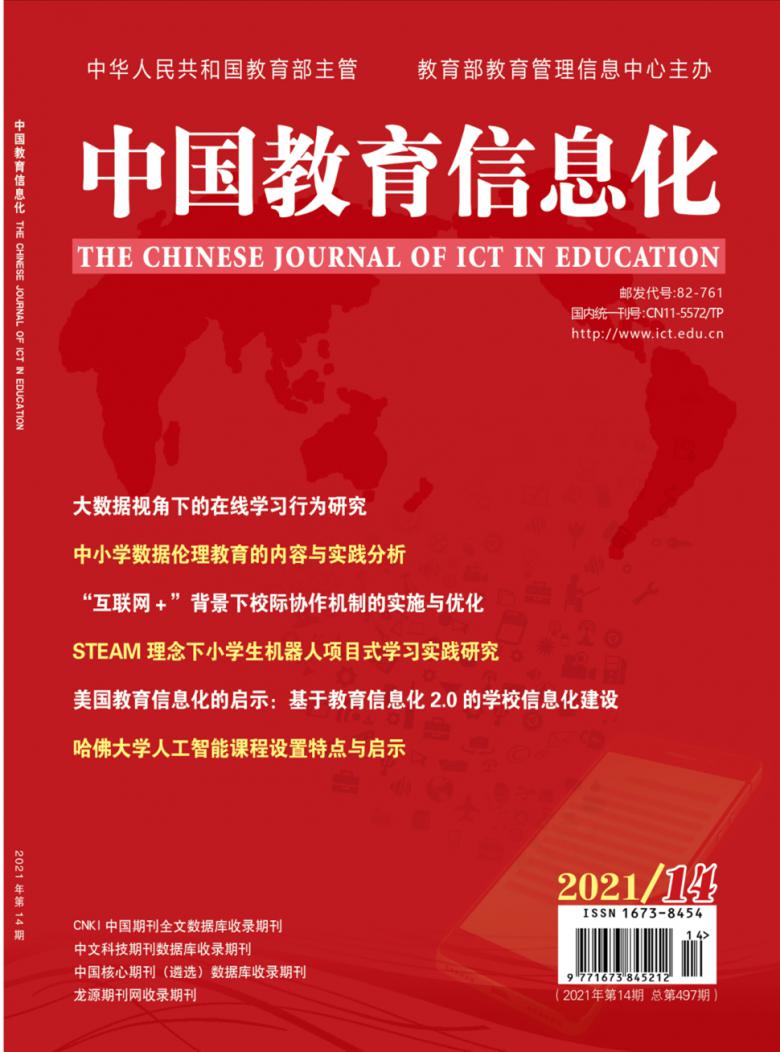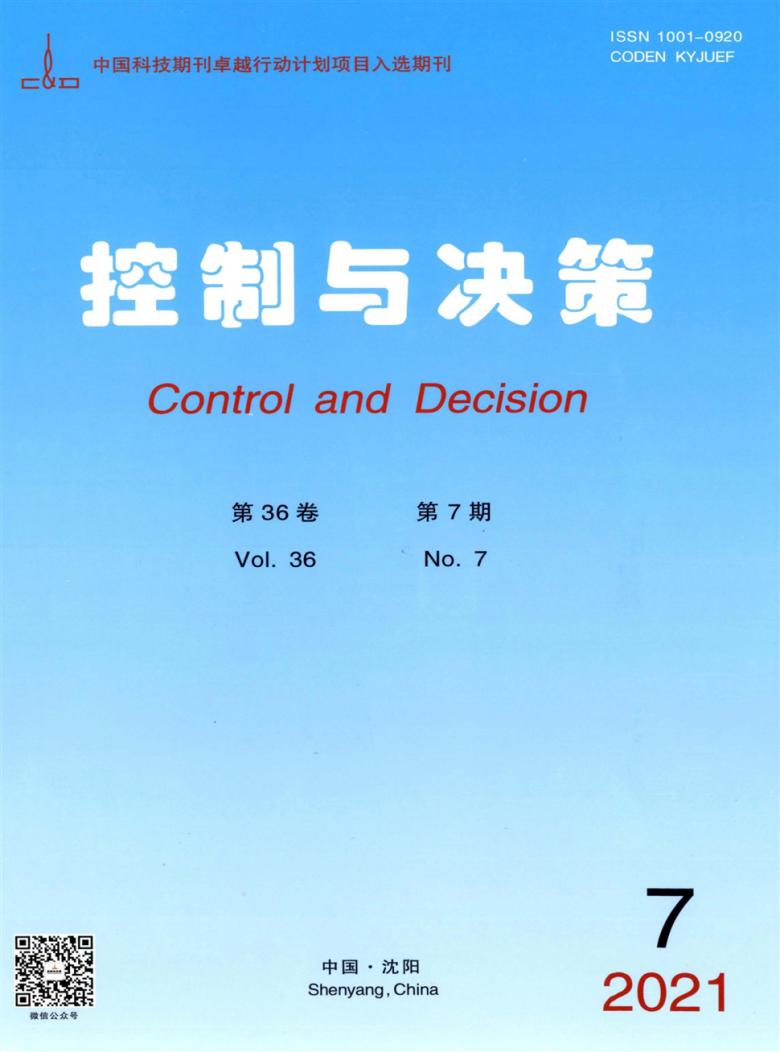摘要:新世纪以来,“启蒙反思”的深入讨论使我们对继续启蒙有了更多的自信。将启蒙与“三农”问题这个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启农民启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诉求。当前农民启蒙如何可能?首先必须围绕农民主体性建设这个核心任务展开,不能落在“你蒙我启”的思维窠臼里,同时又不能独断地将农民启蒙界定为农民不需经别人引导而实现的自我启蒙,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在农民启蒙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坚持“吃透两头”的路径,一头是启蒙者,一头是农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开启当前中国农民启蒙。
一、“农民启蒙”的概念界定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外旨在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各种思潮渐次兴起,以批判工具理性的方式,对表现为启蒙话语霸权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批评和质疑,形成了“启蒙反思”的思想热潮。这股潮流裹挟着批判、质疑、否定的激情,很快波及到国内启蒙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启蒙反思”进行了深入的、持续至今的探讨。首先,对启蒙心态进行了批判:质疑其过分关注物质主义导致严峻的生态环保问题,过分强调个人主义造成了对现代社群的伤害;同时,从过去的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都与这种以“追求富强”为目标,带有侵略性的浮士德精神有关。正是在这种“启蒙心态”的支配下,引发了今天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与问题。其次,围绕现代性危机,开始思考西方已经成就的现代性正面和负面的资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能够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之下展现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成就一种更加合理的现代性价值内涵,“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构新的文明秩序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再次,厘清了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基本达成了共识:不论是西方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全盘否定,还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都是应该反思与清理的,当前重启启蒙应该“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抉出其中具有启蒙含量的精神价值因素,并对这些价值因素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最后,针对中国启蒙运动进程中的问题,提出“五四”和“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品”,今天应该选择正确的启蒙之道,“重建启蒙精神”,追求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在反思启蒙中继续启蒙,但启蒙的理论和启蒙的实践有着巨大的反差,启蒙应该和中国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
毋庸置疑,时贤在启蒙反思中已经收获颇丰,使我们对今天继续进行启蒙有了更多的自信。继续进行启蒙,必须将启蒙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已经成为学界对当前中国启蒙的基本认知。应该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实际问题。因此,将启蒙与农民问题相结合,“农民启蒙”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但是,目前学界尤其是启蒙理论界还鲜有“农民启蒙”这一提法,究其原因,启蒙来到中国一开始就自然地包含着对无法运用自己理性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启蒙,所以提出“农民启蒙”概念好像多此一举,此为其一;其二,启蒙从更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当然地落在作为启蒙主体的社会精英、知识精英身上,更多地强调社会精英、知识精英在对社会深刻分析、全面认知的基础上,提出能够引导普通民众走出“不成熟状态”的思想,跟启蒙的客体(对象)好像瓜葛不大。其三,从历史上来看,农民常常扮演的是被迫害、被拯救、被号召、被教育、被建设、被代言、被救济的角色,很少有将农民与启蒙相联系,提出农民启蒙这一概念。但是,从现实来看,“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如果农民不能摆脱“被”的角色,缺乏独立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自主性,则不能发挥其伟大的创造性,从而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因此,我们提出“农民启蒙”这一概念,目的在于突破“启蒙”的狭义界定,将农民在各种思想观念、政策措施的引导下,不断突破既有“成见”的束缚,从蒙昧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中走出来,敢于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和批判,认知自身的存在状态、确认自身的价值认同方式,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对现代性形成正确认识并努力投身其中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的过程,通称之为广义的“农民启蒙”。广义的“农民启蒙”,一方面既当然地包括农民在现代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引导下,逐步走出蒙昧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实然地包括针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制订以及贯彻落实,比如“三下乡”这种各种惠农措施其实正是潜移默化的农民启蒙。这符合马克思把人的自由问题(启蒙)看作是实践领域的问题,将理性、认识、实践相统一,通过实践实现启蒙,达到人的自由的观点。
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入到“农民启蒙”的概念中,随之又会面临新的责问,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究竟是什么关系?因为,学界通常认为启蒙是自由主义高扬的旗帜(自由主义以启蒙为天职的),马克思主义则对启蒙则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的问题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钟明华等认为,“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但继承了启蒙而且超越了启蒙,从而实现意识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邹诗鹏指出,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当然这种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的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都凝聚着对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与追求。在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乃至当前要继续的启蒙,马克思主义都应该并且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主导角色。尽管在近现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中,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并不能简单断定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不相容甚至是反启蒙的,新时期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其它流派(尤其是自由主义)对于启蒙的研究、克服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推动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稳步前进。
从概念上厘清了“农民启蒙”,从理论上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的关系,随即“农民启蒙”就成为一个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相对于中国启蒙的远未完成,中国的农民启蒙更像一块正待雕琢的璞玉,亟待我们认真打磨!那么,作为这一问题的逻辑前提,我们必须追问:当前重启启蒙应该“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抉出其中具有启蒙含量的精神价值因素,并对这些价值因素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最后,针对中国启蒙运动进程中的问题,提出“五四”和“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品”,今天应该选择正确的启蒙之道,“重建启蒙精神”,追求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在反思启蒙中继续启蒙,但启蒙的理论和启蒙的实践有着巨大的反差,启蒙应该和中国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毋庸置疑,时贤在启蒙反思中已经收获颇丰,使我们对今天继续进行启蒙有了更多的自信。继续进行启蒙,必须将启蒙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已经成为学界对当前中国启蒙的基本认知。应该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实际问题。因此,将启蒙与农民问题相结合,“农民启蒙”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但是,目前学界尤其是启蒙理论界还鲜有“农民启蒙”这一提法,究其原因,启蒙来到中国一开始就自然地包含着对无法运用自己理性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启蒙,所以提出“农民启蒙”概念好像多此一举,此为其一;其二,启蒙从更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当然地落在作为启蒙主体的社会精英、知识精英身上,更多地强调社会精英、知识精英在对社会深刻分析、全面认知的基础上,提出能够引导普通民众走出“不成熟状态”的思想,跟启蒙的客体(对象)好像瓜葛不大。其三,从历史上来看,农民常常扮演的是被迫害、被拯救、被号召、被教育、被建设、被代言、被救济的角色,很少有将农民与启蒙相联系,提出农民启蒙这一概念。但是,从现实来看,“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如果农民不能摆脱“被”的角色,缺乏独立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自主性,则不能发挥其伟大的创造性,从而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农民启蒙”这一概念,目的在于突破“启蒙”的狭义界定,将农民在各种思想观念、政策措施的引导下,不断突破既有“成见”的束缚,从蒙昧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中走出来,敢于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和批判,认知自身的存在状态、确认自身的价值认同方式,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对现代性形成正确认识并努力投身其中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的过程,通称之为广义的“农民启蒙”。广义的“农民启蒙”,一方面既当然地包括农民在现代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引导下,逐步走出蒙昧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实然地包括针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制订以及贯彻落实,比如“三下乡”这种各种惠农措施其实正是潜移默化的农民启蒙。这符合马克思把人的自由问题(启蒙)看作是实践领域的问题,将理性、认识、实践相统一,通过实践实现启蒙,达到人的自由的观点。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入到“农民启蒙”的概念中,随之又会面临新的责问,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究竟是什么关系?因为,学界通常认为启蒙是自由主义高扬的旗帜(自由主义以启蒙为天职的),马克思主义则对启蒙则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的问题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钟明华等认为,“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但继承了启蒙而且超越了启蒙,从而实现意识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邹诗鹏指出,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当然这种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的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都凝聚着对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与追求。在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乃至当前要继续的启蒙,马克思主义都应该并且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主导角色。尽管在近现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中,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并不能简单断定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不相容甚至是反启蒙的,新时期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其它流派(尤其是自由主义)对于启蒙的研究、克服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推动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稳步前进。从概念上厘清了“农民启蒙”,从理论上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的关系,随即“农民启蒙”就成为一个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相对于中国启蒙的远未完成,中国的农民启蒙更像一块正待雕琢的璞玉,亟待我们认真打磨!那么,作为这一问题的逻辑前提,我们必须追问:当前“农民启蒙”如何可能?
二、主体性建设——农民启蒙的核心任务
肇始于西方以理性自觉为核心、以科学为真理、以自由为目的、以反思批判为手段的启蒙,自近现代移植到中国就偏离了西方启蒙的本土意义,当中国近代开始启蒙的征程时,它已不完全是西方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启蒙,而更多的是作为民族救亡和追求富强的启蒙,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意义上的启蒙。[61所谓实用理性意义上的启蒙,实际上是指把启蒙作为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任务的工具,是以民族、国家觉醒为宗旨,而不是以个体的觉醒为依归。当救亡上升为近代中国的优先主题时,并没有中止启蒙,某种程度上来说,救亡也是一种启蒙。民族救亡是要通过整个民族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政治运动来实现的。当这种运动裹挟了启蒙,就忽略了对个体自由这个启蒙的最终目的的追求。虽然个体自由是以民族独立为前提条件的,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却是根本的目的。启蒙,既要保证个体行为思想的自由,又要实现社会公平而有序。政治性的革命运动往往是狂热的,其必然导致在启蒙中理性自觉的缺失,未能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过滤,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吸收,导致启蒙的“理性缺位”(姜义华语)。同时,中国近代的启蒙,不论是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受汉语语境里启蒙是由权威单向度地向被启蒙群体进行思想的教育或传播语意的影响,均渲染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一味强调上层知识精英对普通大众的教育与引导,广大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幻想站在一个空旷无比的广场上,头顶湛蓝的天空,明朗的太阳,脚下匍匐芸芸众生,仰着肮脏、愚昧的脸,惊讶地望着这些真理的偶像”,而未真切地探究普通大众的所思所想,甚而将自己与他们对立起来,只注重对其进行单向度的启蒙教育。以上诸种因素的合力,形成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中国近现代主流启蒙话语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中,迎合了急于跨入现代化门槛的社会心理,继续发挥作用,乃至持续影响到今天我们仍要继续进行的启蒙。
新世纪以来,“农民启蒙”的推动更多地呈现在政府主导的破解“三农”问题各项重大战略决策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小城镇建设以及历年的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上。但是,这样的启蒙由于受中国启蒙主流话语言说方式的影响,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政府对农民的单向度的启蒙倾向,表现为政治性的运动,一味地将农民作为被启蒙群体,将农民启蒙裹挟到现代化的进程中,武断地对农民实施各种强迫性的启蒙,未能注意到农民自身主体性的确立。这就导致农民启蒙乃至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必然出现诸多问题,一方面农民对突袭而来的各项惠农措施漠然置之,另一方面也就延滞了农民启蒙的推进。
面对这些令农民闹心、令执行者(启蒙者)委屈的问题,我们应该反思中国启蒙主流话语的言说方式。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的两次启蒙运动中,由于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启蒙被当作工具,偏离了启蒙原有的本义,那么,在新阶段,当我们已经实现了两大历史任务,正在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奋进的过程中,启蒙应该打破“鲜明的国家本位”、回归其本义,应该是“自然、自发、在日常进行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久远历史价值的精神和心智活动”,是在稳定的环境中把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指向广大农民,而不再将“农民启蒙”依赖于一场政治性的运动。启蒙不是运动,当前中国农民启蒙也决不应该仅仅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而应该是长期的“润物细无声式”的祛魅过程。
这种“祛魅”应该走出近代以来“因乡村建设而致乡村破坏”的悖论,打破“鲜明的精英意识”,着眼于农民的思想状况实际,积极培育、塑造农民的主体性。质言之,“农民启蒙”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建设农民的主体性。“农民主体性从酝酿、萌芽、发生一直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并未完全确立,并将继续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要能够发挥作为农业现代化主体的力量,前提是其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建设农民的主体性,首要任务是保证农民个体的独立思考,树立其价值选择的自主性,而不是强行代替他们做出各种生产、生活上的安排。新形势下,只有农民真正发挥其创造性的主体力量,才能够在建设和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的过程中,逐步从前现代的认知模式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启蒙。惟有这样,在当前农民启蒙中,农民才可能跳出“被”(被迫害、被拯救、被培育、被启蒙等)的角色!
三、思想引导——农民启蒙的必然要求
我们批评中国近代启蒙中的精英色彩,突出强调当前农民启蒙应该围绕农民的主体性建设这个核心任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强调让农民实现自我启蒙?
尽管“启蒙既不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纯粹运动,也不是人类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教化。”就此而言,当然应该反对启蒙中的精英色彩,否认启蒙是上层精英对被启蒙者的单向度教育。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启蒙确实需要有首先开蒙的人引导,康德关于什么是启蒙的回答中明确指出:“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不成熟状态”在中国近现代就是大多数国民无法或者没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西方现代文化对民族、国家、个人的影响,这就需要首先睁眼看世界的人加以引导。与西方的启蒙运动以理性怀疑精神批判宗教信仰和神圣崇拜不同,中国的启蒙是以西方的现代思想体系作为批判和介入社会的武器,清除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所造成的愚昧和黑暗。如果说西方的启蒙是要将人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么中国的启蒙则是从一开始就是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是与传统的断裂。相较于西方对上帝的批判,中国启蒙对传统的批判要显得困难得多,因为“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并“溶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远比刚刚从西方移植的现代文化要深厚结实得多、也牢固而又顽固得多;同时,中国近代的现代性启蒙又是被迫的,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要进行顽强地抵抗,这就势必给“农民启蒙”批判传统糟粕、蒙昧造成很大的困扰。农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强固守者,对传统规范性文化和非规范性文化具有极强的依附性,更需要有人加以引导,从这种依附心理中走出来,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走出不成熟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逐渐向现代化迈进,但一定程度上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上,其思想观念的却远远不能与之相契合。换言之,农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紧张,大多数农民仍旧茫然于物质富裕与精神迷茫之间的巨大紧张而无力消解。“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农民不能对现代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形成正确的认识,那么必然造成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茫然失措于各种现代化的陷阱,比如物欲主义、工具主义、大众文化等等。因此,当前的农民亟需要由人进行引导,走出对现代化认知的“不成熟的状态”,规避其落人现代化的陷阱!
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消除农民启蒙中的精英色彩,强调农民启蒙应该围绕主体性建设这个核心任务展开,不能落在“你蒙我启”的思维窠臼里;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农民启蒙中又不能独断地将其界定为农民不需经别人引导而实现自我启蒙。这样,农民启蒙就好像陷入了既要维护农民的主体性又要需别人引导的两难困境之中。如何破解这个悖论,使农民启蒙走出这种困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四、“吃透两头”——农民启蒙的现实路径
“启蒙者不能置身启蒙范围之外,单纯以启别人之蒙为职志,他本身既是启蒙的行动者、也是启蒙的对象。既然启蒙者既是启蒙的行动者、也是启蒙的对象,那么当前的农民启蒙应该是“有蒙共启”。“有蒙共启”——这是我们破解上述悖论的正确路径。“有蒙共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晏阳初先生提出的:“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当然所谓的“农民化”,并不是要求转身变为农民,而是要深入农村生产生活,充分了解农民的所需所求、所思所想,认真研究农民的实际生存和现实心理,切实掌握农民对现代化形成的偏差乃至错误认知,从而引导他们规避落人现代化的陷阱,实现在农民启蒙中“有蒙共启”。
如何“农民化”,如何实现“有蒙共启”,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陆学艺先生的“吃透两头”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所谓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坚持“吃透两头”,就是要对中央的精神(“上头”)和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头”)做真正、全面、准确的了解,其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三农”问题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的指导下,开发广大农民的主体性力量,从而真正促进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陆学艺先生的“吃透两头”,另一方面要在启蒙实践中“吃透两头”。
当前,从理论上来讲,农民启蒙应该坚持“吃透两头”。一头是在研究启蒙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启蒙在中国当下所遭遇的各种挑战,包括后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大众文化、多元现代性等,解开“古今中外”相互纠缠的死结,重新确立启蒙的合法性基础。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界已进行了深入持久且富有成效的探讨,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当下我们仍处于现代化的成长与成熟过程中,不能不加分析她将后现代主义移植到当下中国社会而否定启蒙(庞学铨);正确的启蒙与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高全喜),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经受启蒙之理性主义的洗礼,才能“兼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张志伟);而大众文化在当前的步步紧逼是启蒙面临的最大难题,其攫取利润的主要动机促使它必然要迎合大众的需要和口味,从而使文化本身失去了自足性和自律性,走向平庸和媚俗,而平庸和媚俗对于农民启蒙而言更是一味绝命毒药,如何能够发扬启蒙精神,研究合理地从传统中汲取资源和智慧的方法,构建中国式的现代性,开启一种真正的启蒙,从而破解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对农民启蒙的冲击,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对农民启蒙进行研究,另一头要首先厘清农民启蒙的内涵与外延,研究中国农民启蒙的历史衍变,掌握农民启蒙在近现代历史上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民启蒙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中的农民启蒙,以及新时期以来农村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启蒙,实地调研掌握当前农民的实际境况,建设适合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文化,切实推动中国农民启蒙。
从实践中来讲,农民启蒙坚持“吃透两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就作为知识精英的启蒙者而言,应该禀持在农民启蒙中启蒙自己的原则,围绕农民主体性的建立这个核心内容,营造一种自由和宽容的思想氛围,保证农民的独立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自主性,进而引导农民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而摆脱“不成熟状态”,“只有在一个宽容的环境中,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才能充分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才能真正实现康德所说的不受任何人的支配而自由地行使自己的理性权利。同时,要走出书斋,响应温铁军教授提出的“用脚做学问”,象曹锦清教授一样,真正走到中国各地的地头田间,走向农村的街头巷尾,坐上农户的炕头,将自己化身为农民,切身感受农民冷暖、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切实掌握现代文化对农民的影响、农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众文化对农民的冲击,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启蒙农民的措施,在不抹杀其主体性的前提下,引导农民正确认识现代精神,规避其走向现代化的陷阱;消除大众文化的平庸媚俗对农民的消极影响,将传统的农业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洗礼,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农民的炕头上才能做好农民启蒙这篇大文章!
其次,就惠农政策的基层落实者(启蒙者)而言,应该祛除将惠农政策对农民遮遮掩掩的狭隘偏见。相比于城市,惠农政策在广大农村的贯彻与落实是对农民进行潜移默化的最好启蒙。但要成为最好启蒙,作为惠农政策的基层落实者一方面必须真正吃透各项惠农政策,深刻认识各项政策制定的目的、意义,另一方面必须结合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从而制订政策落实的合理措施,并将国家的惠农政策以及落实措施对农民进行宣讲,切不可不考虑农民作为主体的价值选择而单方面强迫执行,以至于使惠农措施得到的是农民漠然的回应,甚者会造成群体冲突事件。因此,应该切记“混沌之死”的警示,绝不能用“倏”、“忽”“造福混沌”的方式主观武断地造福农民!要想从根本上祛除新农村建设中“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弊病,就必须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出发,激发农民积极参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不能单方面通过外在的强制落实惠农政策。各项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了农民个体的独立思考,注重了农民价值选择的自主性,既可以使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也能够在这一过程中使农民得到启蒙!
再次,就农民启蒙的方式而言,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的“催化剂”,是当前能够将启蒙思想送达农民的最好方式。美国社会学家罗吉斯·伯德格在《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农民传播了现代道德,大众传播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传播了信息,说服农民接受变迁。当前,随着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推进,尤其是电视、手机、新媒体等在内的现代传播媒介开始被广大农民所掌握,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农民的交往范围、丰富了农民的信息交流渠道。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的社会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生存方式从依附性向自主性转变。就此而言,大众传媒为当前农民启蒙提供了通畅的渠道,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农业发展理念、农村发展成就、农民致富经验等等通过这一通畅的渠道快捷地传达到千家万户的农民心中,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农民启蒙。但是,当前农民启蒙在运用大众传媒的过程中,同样要坚持“吃透蘧头”的理论。一头要吃透大众传媒对农民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不能让大众传媒成为平庸、媚俗的大众文化的传播渠道,将很多负面的、恶俗的、暴力的、色情的等为吸引农民眼球的内容撒向广大农民,不但未能实现农民的启蒙,反而会严重污染农民原有的精神世界,引发更多新问题与新危机。换言之,不能让农民被负载大众文化的传媒本身所征服,使农民从对传统的依附又转向了对大众文化的依附,刚刚确立的自主性又再次遭到破坏,从而失去进行自我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能力,又将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拱手交于大众传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农民启蒙运用大众传媒推进自身发展时,就必须吃透另一头——农民。农民启蒙要借助大众传媒这个方式,一方面必须了解掌握当前农民的所需所求、所思所想,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为农民提供其喜闻乐见的、健康向上的、提升农民主体性的文化艺术作品,从两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提升农民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必须净化大众传媒所输送的信息,严格控制各种对农民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的传播,为农民启蒙营造良好的精神氛围。
唯有如此,当前农民启蒙才能成为可能。